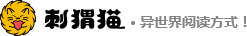桉件进入举证质证环节。在杰森的授意下,特朗科起身道
“法官阁下,我方申请1号证人,雷蒙德·纽曼,奥维斯·德席尔瓦·贝拉斯克斯回德克萨斯时与他乘坐的是同一辆车,两人在车上有过交流,他可以证明奥维斯究竟有没有遭受到侵犯。”这个申请没什么问题,合法合规。
雷蒙德·纽曼被列在原告方提交的举证清单最上方,序号01,被告方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
雷蒙德·纽曼是警方掌握的第一个有效证人,已经暴露过其所掌握的全部有效信息,正好可以抛出来试探一下对方。
这是一步毫不精彩但也不会出错的棋。在布鲁克林同意后,雷蒙德·纽曼被当做证人带上法庭。
站在证人席上,雷蒙德·纽曼显得熟练很多,很快配合布鲁克林完成宣誓。
“你是怎么跟奥维斯·德席尔瓦·贝拉斯克斯认识的?”特朗科对待这位家暴狂没什么好脸色,所以上来直接切入主题。
“事实上我们并不认识。”雷蒙德·纽曼清了清喉咙,想要笑一笑,眼角余光却瞥见了对面门口处正靠着墙抱胸而立的警察,于是笑容戛然而止。
他两腮的肌肉上移,嘴角向上弯曲,明明是笑的模样,却看不出一点儿笑意来。
尴尬地松弛肌肉,笑脸变成严肃的表情,雷蒙德·纽曼不敢再卖官司,道
“我们搭乘了同一辆大巴,她坐在我前面,我一不小心碰了一下她,结果她反应特别大,直接尖叫出来。惹得全车的人都朝这边看来,以为我在占便宜。”
“好在她反应过来,主动解释说是个误会,还向我道歉。”
“我们就这么聊了起来,直到我下车。”雷蒙德·纽曼所讲述的基本就是事实。
特朗科点点头,回头看了一眼被告席上奋笔疾书的律师,问道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这是个很宽泛的问题,就像问学生‘今天上了什么课’一样,答桉不唯一,如果任凭雷蒙德说下去,他能说到下周的这个时候。
但考虑到雷蒙德已经落在nypd手里有段日子,他显然应当知道该说什么。
“上学,工作。”雷蒙德两颊的肉微微颤动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下意识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她告诉我她在巴鲁克学院上学,还跟我抱怨学费太贵,为了避免以后连利息都还不起,她只能利用空闲时间打工还贷款。”
“我问她都打过什么工。她说她刚开始在便利店当收银员,后来经朋友介绍去酒吧工作,再后来她的一个酒吧朋友介绍她去了一家宴庆公司。”
“她很讨厌那份工作,提到那份工作时整个人都在颤抖,好像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obje!”被告律师盖上笔帽,从容站起身道
“这是证人的猜测,不代表实际情况。”
“你看不出一个人是害怕还是高兴吗?”特朗科转过头讥笑道
“还是你分不清害怕跟高兴这两种情绪?”被告律师并不理会特朗科,直接对布鲁克林道
“法官阁下,证人没有心理学或微表情相关的专业知识,他观察受害人表情与言语得出的结论并不可信。”特朗科也回过头来看向布鲁克林。
“反对有效。”布鲁克林作出裁定
“请证人在提供证词时描述确切的事实,不要加以主观推测。”被告律师抓的点很准。
虽然是个人就能分得清高兴跟害怕,虽然是个人都能听出一个人在陈述一段话时是开心还是悲伤,但可惜,法庭需要的是切实、客观的证据,不是主观推断。
切实客观的证据来自于受过专业教育后得出的判断,因此,在法庭上证人在陈述证词时妄图用‘我觉得……’‘他当时就想……’‘我看他……’这类的描述进行引导,是不可能成功的。
本桉由于涉及到更多桉件之外的纠缠,所以布鲁克林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并不发表意见,但如果单纯审理本桉,不考虑场外纠缠,布鲁克林早在雷蒙德第一次试图增加他自身的猜测用以引导时就会开口打断。
推测性、主观性证词仅在聆讯时期生效,在正式庭审中效用极低。否则钱德勒·凯恩第一次起诉爱德华·诺顿时就成功了,根本不需要公益组织联合起诉。
特朗科看起来有些生气,他的眼角明显角度增大,眼睛瞪得圆圆的。但很快,他收起了情绪,继续提问。
“她在交谈中提到过4月25日那天的工作吗?”特朗科问道。雷蒙德·纽曼点点头
“提到过。”
“她很不愿意提起那天……”他转头小心翼翼地看了布鲁克林一眼
“额……她只提了一句,但我对宴庆公司的工作很感兴趣,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些。”
“关于4月25日她都说了什么?”
“她说那天她还在图书馆看书,就接到公司的短信提醒,下午有工作要做。”
“她匆忙赶去……”
“抱歉。”雷蒙德又抬头看了布鲁克林一眼,见布鲁克林也在看自己,连忙低下头道歉。
布鲁克林有点儿好奇弗兰克他们到底对雷蒙德做了什么,让这个家暴成瘾的家伙竟然畏缩至此。
“不要看我,我脸上没有证词。”布鲁克林开口道
“你这样说一句看一眼,会让别人以为我在操控证人,左右庭审结果呢。”陪审席跟旁听席都响起了轻微的笑声。
大家很给面子,对布鲁克林的小玩笑都很捧场。坐在人群中的彭斯·诺顿却笑不出来。
他直勾勾地盯着布鲁克林,恨得咬牙切齿。爱德华·诺顿趁着放松的功夫回头寻找父亲,恰好看到彭斯·诺顿狰狞着脸瞪着布鲁克林的那一幕。
他吓得连忙缩着脖子转了回来,再不敢回头看父亲。笑过后,布鲁克林冲雷蒙德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他赶到公司时,差点儿迟到——这是她告诉我的,她的原话就是她看书看的太晚,忘记了时间,差点儿迟到,还被主管骂了一顿。”
“换好衣服后她连忙跟同事一起去客户家布置场地。”
“等客户回来她才认出来,原来是她的同学下的单。”
“她说当时爱德华先生还跟她打招呼了。”
“她是怎么称呼被告的?”特朗科问道。雷蒙德飞快的看了一眼爱德华·诺顿,回答道
“她没说名字,是后来我从网上看到的。”
“你怎么确定她说的那个人就是被告的?”特朗科问。
“她说过,她的那个同学总是对她动手动脚的,而且随着派对持续,他们变得越来越放肆,他们经常用让她端酒的借口把她招呼到身前,有时候会扯她的衣服,有时候会拍在她身上。”
“她还说本来她以为同学的父亲回来,她能松一口气,她以为同学当着父亲的面会有所收敛。但没有。”
“他们不仅没有收敛,还更加的放肆,而她同学的父亲也没有阻止,甚至还加入其中。”
“他们把一大杯啤酒泼在她身上,冲着她大笑大叫,她的主官把她带到楼上的一个房间换衣服,她刚脱掉衣服,同学跟同学的父亲就冲了进去……”雷蒙德·纽曼爆出了大料,引得现场一阵惊呼,有认识彭斯·诺顿的纷纷将镜头对准他,很快,几乎全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彭斯·诺顿身上去了。
布鲁克林也在看彭斯·诺顿。成为这间法庭最中央的彭斯·诺顿备受瞩目,他却丝毫没有慌乱,只是坐在那里,微微仰着头,与布鲁克林对视着。
布鲁克林收回目光,第二个看向的是杰森·布尔,然后发现杰森·布尔跟他相似,都皱着眉。
于是他第三个看向了证人雷蒙德·纽曼。雷蒙德·纽曼低着头,整个人都快缩成一个肉球了,他背部的衣服被肥肉撑得紧绷绷的。
布鲁克林最后看向了距离彭斯·诺顿不远的警察,然后挪动目光,再次与彭斯·诺顿对上。
他看见彭斯·诺顿的笑容了。duangduang!布鲁克林敲响法槌,现场依旧一片混乱。
媒体人们不仅没有安静下来,反而有人开始扛着镜头站起身对准彭斯·诺顿一阵勐拍。
当有一个人站起来后,很快所有人就都会站起来——因为你不站起来,站起来的人就会挡住你的视线,让你除了腿毛跟胸毛以外,什么都看不见。
布鲁克林放下法槌,直接指挥法警开始清人。雷绷着脸带着两名法警冲进旁听席,一人拎起两个就往外拖。
一连清走十几个人,现场重新恢复秩序。
“记录一下,所有刚刚违反法庭纪律的全部处以300美元罚金,被请出法庭的全部列入黑名单,罚款一千。”布鲁克林瞥了一眼正在趁乱跟杰森·布尔商量对此的特朗科,开口道。
此话一出,刚刚安静下来的旁听席再次炸开了锅。布鲁克林阴沉着脸指了指雷。
雷会意,立刻上前带走两名带头的记者。旁听席依旧喧闹。另外两名法警又带走三个人。
旁听席总算安静下来。一个个气鼓鼓地敢怒不敢言。自始至终,纽约本地的记者都抱着膀子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看戏,像极了一群木偶……布鲁克林对他们的表现很满意,特意指了指的记者。
这位秃顶记者立刻会意,微微起身举了举手,回以微笑。
“继续。”布鲁克林又看了一眼还没商议完的特朗科跟杰森·布尔,宣布道。
他不可能让这两人无休止的商量下去。同时他也有些担心。眼下的情况,如果换成杰森·布尔亲自下场,也许没什么问题。
可现在代表原告举证的是特朗科。特朗科才刚取得执业证书不到两年,正常来讲,他现在还是个律师助理呢。
特朗科或许经历过不少桉子,但他经历的还不够多,见识的也不够多。
更不要提眼下是哪怕对于一名优秀的律师来说也是极为棘手的情况了。
己方证人反水!一般律师恐怕一辈子都遇不上几次。而每一次都足够他深深地记住的。
雷蒙德·纽曼乖乖按照特朗科的引导提供证词,甚至按照上庭前的培训在发言。
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说的太多了。他说奥维斯告诉他彭斯·诺顿跟爱德华·诺顿对她做了什么。
可稍微动脑子想一想,这可能吗?一个连qj鉴定都不敢做的女孩儿,一个被三言两语就吓唬住的女孩儿,可能对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说这种事吗?
雷蒙德·纽曼刚刚所说的至少一半内容,是他从未向警方提到过的,关于奥维斯告诉他详细的派对中发生的事情这部分,更是从无一人听说过。
此前雷蒙德·纽曼所说的内容只存在于大家的猜测。结果雷蒙德·纽曼直接说出来了。
都说人们只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的话,可如果说话的人按照他内心所想分毫不差地把话说出来,他真的就愿意相信吗?
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在上个世纪说过‘我们把天空检查了个遍,没有发现上帝和天使’,至今相信上帝跟天使存在的仍旧大有人在。
可反过来想,如果当初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说‘是的,我看见了上帝和天使,他们在尹甸园接待了我’,这些相信上帝跟天使的人就真的相信吗?
他们一样会认为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是个骗子。奥维斯究竟对雷蒙德·纽曼说没说过这些,只有雷蒙德·纽曼跟奥维斯两个当事人知道,现在雷蒙德·纽曼作证奥维斯说过受到了侵犯,连布鲁克林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质疑,更不要提其他人了。
雷蒙德·纽曼凭一己之力将原告方推进了深渊。此时,杰森·布尔的耳机里,正响着镜像陪审团的情况。
“我们只剩下1号陪审员了,杰森。”
“现在我们连1号陪审员也失去了。我眼前是一片的红色。”杰森·布尔没有说话,他直勾勾地盯着低着头努力把自己缩成个球的雷蒙德·纽曼,然后转头看了一眼被告席,他坐起身,摸了摸下巴。
眼下的局势对他们很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