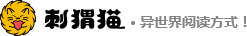第十五章 心贼难破
舞妓先是上前盈盈一拜,眉眼间带着万种风情,说道:“奴名唤杨柳,是这扶风院里的花魁娘子。这段舞是奴幼年时在戏班所学。”
李穆白接着问:“跟何人所学?什么戏班?”
杨柳答道:“奴当时跟戏班里面一个唤做玉娘的伶人习舞,老班主还用这段舞排了出皮影戏呐。不过,只是蜀州一无名的杂戏班罢了,但据说这老班主的儿子后来拜了高人学艺,学成后在京城成立了有名的雁影戏班。”
原来如此,什么玄女起舞,不过是一场皮影戏罢了。
那天根本不是因为当时天色已晚,才看不清玄女的相貌,是因为这利用烛光的投影,只能照出个人偶的轮廓。
至于那灵棚就更好解释了,白布本身就是现成的工具。
谢含辞从怀里掏出一截人偶的手臂:“这是我在火盆中找到的,除了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未烧尽的碎木渣子。我开始以为是给巡抚夫人烧的纸人纸马之物,现在想来应该是戏班做的道具。”
谢含辞抬头看向李穆白:“只是我还有一事不明。”
李穆白把玩着刚才从谢含辞手中夺来的酒杯,问道:“何事?”
谢含辞吐出两个字:“动机。”
李穆白低头将里面的酒一饮而尽:“这次南境进的贡品里有一件极要紧的东西,京城里的人害怕,所以让刺客冒死来偷。这里的人也害怕,所以他们宁可杀害父母和枕边人,只为了躲开押送这件差事。”
谢含辞只觉得那酒烈得要命,她只喝了一口就有些上头,鬼使神差地问道:“那你不害怕吗?”
李穆白看她脸颊泛红,眼波似水,知她是喝醉了,倒了杯茶递给她:“怕,但是我不能退。”
楼下的客人一阵骚动。
“快看啊,那是什么?”
李穆白将窗推开,只见扶风院二楼的白墙上也出现了玄女起舞的奇观。
李穆白拿出了一件斗篷,递给菁菁:“给你家小姐穿上,吃了酒见风小心明日头疼。”又对谢含辞说道:“你怎么样,还能办案吗?最后一场戏,你要不要跟我去看?”
谢含辞原本已经有些迷糊,听到“办案”两个字突然来了精神,顿觉酒都醒了大半。
李穆白将谢含辞带进了三楼的客房,一个翻身上到了房梁。刚坐稳,飞云门门主便推门走了进来,谢含辞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大胡子。
他似乎有些醉意,进门便躺倒在了床上。过了一炷香的时间,门外传来了两声敲门声,大胡子不耐烦地问道:“谁呀?”
“是我,岳父。”来人正是张巡抚。
大胡子骂骂咧咧地起身开门:“这么晚了,你来做甚?你还有脸来找我?”
张巡抚身边只带了个随从,这随从全身被披风包裹着看不清面容。进门后,二人坐在了珊瑚炕桌上,随从则安静地站在了一旁。
大胡子只给自己倒了杯茶,饮了一口,对张巡抚说道:“我义女到底是怎么死的?你若想跟我扯什么玄女就歇歇吧,今日那装神弄鬼的戏子已经被我抽了个半死。就这么点伎俩,蒙别人还行,老夫可在江湖上混了六十载。”
张巡抚也给自己倒了杯茶:“小婿不敢欺瞒岳父大人。云芝的死,却与我有关。但也是逼不得已,牺牲云芝一人,总比满门抄家灭族要强。王家那老妇不在了,以后王家都是云芝的女儿掌家。我和云芝没有儿子,不然巡抚府的家业我也都会交给她儿子的。”
大胡子紧紧攥着手里的茶杯:“你当我飞云门是吃素的吗?我的义女你说杀便杀。你俩为什么没儿子,还不是因为你那宠妾?我昨日将云芝身边的丫鬟绑了来,她全招了,她是你那宠妾插在云芝身边的人,你这巡抚当得真是糊涂啊!”
张巡抚依旧慢条慢条斯理地品茶:“岳父,原来当我不知呀?这丫鬟就是我帮着插进去的,那些避子的药自然也是我默许的。我是真怕了,怕你干女儿再生出一个跟她脾气秉性一样的儿子来。”
“你!”大胡子刚要发作,张巡抚先一步将自己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旁边的随从突然暴起,身形如电,挥着手中的短刃向大胡子刺来。
“冯生!怎么是你?”大胡子躲避不及,被利刃划破了胸口,看着眼前熟悉的人,他惊愕道:“我将飞云门的营生都交给了你,那酒庄一年至少可赚万两,平日里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跟他勾结?他许了你什么?”
冯生轻笑着说道:“老门主,他什么都没许我。只是你死了以后,这门主之位,就是我的了。你待我好?你明知我最不耐跟银钱打交道,还让我去打理那些俗物。我从永州跑出来混江湖,是为了做大侠,不是为了做掌柜的!“
说罢,这冯生和张巡抚同时发难,二人武功高强,又年富力壮。渐渐大胡子招架不住了,一记记闷拳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踉跄着后退,撞翻了圆凳,倒在地上。
大胡子躺在地上喘着粗气,看见了房梁上的两人,向上伸手。
谢含辞挪了挪身子,凑近李穆白:“王爷,还不下去救人吗?他快被打死了。”
冯生往地上啐了一口,吐出一颗碎牙道:“这几天连杀两个娘儿们,我都快忘了自己这身武艺,跟你打这一顿也算痛快。别挣扎了,让我一刀给你个痛快吧。门主这手势啥意思呀,求救老天爷?难不成你还指望有人从天而降来救你?”
谢含辞心道你这嘴巴还挺灵验,拉着李穆白的袖口一个翻身从房梁上翻了下去。
李穆白苦笑一声,将她托住。
“你们两个欺负一个老人家有意思吗?”谢含辞对一脸凶相的二人说道。
大胡子气若游丝,但似乎有什么重要话想说,努力地发出声音。谢含辞忙蹲下身,将耳朵凑近。
“我……我还不老。再过两个月才满七十。”
谢含辞:“……”
一盏茶的时间,李穆白便将两人解决。走到窗前,吹了声口哨,三四个暗卫立刻进了屋子,将人带了下去。
五日后,张巡抚在牢里招供,此事均是他和冯生二人谋划,雁影戏班是张巡抚花重金请来的,人是冯生杀的,王参军对此事并不知情。
“你说这王参军真的不知情吗?”谢含辞嘴里叼着荣华酒楼的枣泥酥饼问道。
李穆白摇了摇头:“他去年围剿山贼有功,这是圣上的意思。不管怎么样,他母亲被冯生所害,他确实也是受害者。”
谢含辞啧啧两声,感慨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呀。”
随从上前,交给了李穆白一个竹筒,他打开一看皱起了眉头。
“算上之前那刘副将,押送贡品的武将一下子折了三位,周边的将领都不能用。我向圣上举荐了飞云门,圣上的意思是朝廷的事不能只交给江湖门派,还是需要一位蜀州官员带队。信上,陛下对你的父亲这几年的政绩赞许有加。”
谢含辞一下子食不知味,想将那贡品里的要紧东西问清楚,可又觉得李穆白并不会告诉他,只好问道:“圣旨大概几日能到?”
李穆白答道:“不出五日。”
谢含辞又问道:“我能不能……”李穆白不等她说完,便打断她:“不能。我会护好你父亲的,此去山高路远,京城里也不太平,你就在蜀州城里等着。我保证你爹会安然无恙地回来。”
三日后,不仅是谢含辞吵着要同行,沈淑怡甚至不等谢渊开口就交代下人连自己的衣饰一同打包。
“淑怡,你这别闹。我这是随军押运,哪里能带上妻儿?”谢渊看着沈淑怡的行李说道。
“不带孩子,就我跟你去。三年前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躲开京城里的争斗,如今非回去不可,那这趟就让我陪你走。”沈淑怡看着谢渊,目光炯炯。
谢兰舟也在一旁附和:“父亲、母亲,孩儿也想陪你们同去。”
谢含辞淡定地啃着鳄梨,看着母亲和哥哥吵着要去,她知道闹到最后,父亲也不会答应,这都是白费力气。
她已经想好了对策,趁现在多吃两个新鲜的果子,等她上了路,那可就只有噎人的干粮了。
谢含辞一早留了份手书,让菁菁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给沈淑怡看。那时估计队伍已经到了平关,到时候想追回她已是不可能的了。
李景瑜看着一身伙夫打扮的谢含辞说道:“你真要这样?被发现了怎么办?我可打不过小皇叔。”
谢含辞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没事的,你就说我是你在蜀州城里找的厨子,让我在路上给你烧火做饭吃。你小皇叔天天忧国忧民的,没时间操心你这么点小事。到时候我就跟在你后面的马车就行不会有人发现的。”
李景瑜有些心虚道:“我把你安排进后面的马车倒好说,只是你真的要扮成伙夫,烧菜给我吃?扮成婢女小厮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