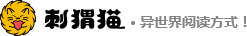侵犯小青的恶棍,乃府里负责膳房采办的小管事。
别看只是一小小管事,这可是肥差,没点裙带关系轻易钻营不来。
而这位小管事的妹子正是老夫人寿安堂的大丫鬟珠翠。
珠翠那位兄长,就是个貌陋的酒色之徒,不是头一次干出这等腌臜事,珠翠已经习惯替他善后。
以往,随手施舍点好处再行威胁一番,就能把事儿轻轻松松给平了。
而今裴姝接替家主之位,新立了府规,又是个冷面不容情的,凡事追究一个对错。
更坏菜的是,她家兄长仅得着一回趣儿,那小蹄子竟意外有了身子。
假若事发,兄长绝计没好果子吃,于是珠翠起了心,随意寻了个错处对小青加以惩戒。
打得就是暗地里弄死小青的主意。
五十大板下去,不信流不掉一块肉,重伤加小产,又得不到医治,必然活不久。
人一死,草席一裹,拉出府草草一埋,谁会在意一个不起眼的烧火丫鬟的死因。
翠珠是万不料,这事竟直直撞到了女君面前,她还特意交代找个隐蔽一点的地方。
众所周知,像后花园这种地方,女君鲜少踏足,一天忙也忙死了,哪有闲工夫逛后花园。
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流年不利寸到家了!
寿安堂里,得了仆妇信儿的珠翠,脑子嗡嗡乱作一团,心不在焉犯了几次小差错。
同是大丫鬟的秋霞纳罕道:“你今儿咋啦?瞧你心神不宁的。”
“家里有点事。”珠翠看了看天色说道:“离晚膳还有些时辰,我想去一趟管事房,老夫人要是唤我,你替我担着点。”
秋霞门清她家兄长是个什么德性,三天不招猫逗狗,反倒稀奇了呢:“成,你去罢,这头有我盯着。”
珠翠行色匆匆去了管事房,掀开门帘就看到她那肥头大耳的兄长,正翘着二郎腿悠哉悠哉吃酒。
珠翠火大,过去一把夺了酒杯:“喝喝喝,你还有闲心吃酒,出大事了!”
旺才张嘴喷出一口恶浊的酒气,不悦皱眉:“一来就抢我酒杯做甚?什么大事,值得你当值的工夫跑来教训我。”
珠翠嫌弃地掩了掩口鼻:“那丫头被女君带去了赜兰居。”
旺才熏红着一张脸,手指抠着鼻孔困惑道:“哪个丫头?”
府里跟他“情投意合”的小丫鬟一只手都数不过来,不说名字,他哪知道指的是谁。
珠翠没好气道:“膳房那个烧火丫头。”
兄长是越来越荤素不忌,那贱胚子干巴巴的,全身上下就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有点可取之处。
珠翠恨铁不成钢道:“跟你讲多少次了,家主换了人,你多少收敛着点。非得在府里头招风惹草,外头有得是勾栏倡寮,你缺那几个银钱吗?”
旺才一听,顿时横眉竖目不干了:“你懂个屁,娼馆里万人骑的脏货,哪比得过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你也不怕你哥染上脏病。”
珠翠闭眼深吸气,要不是亲哥,真不耐烦管他的破事。
旺才满不在乎道:“出息,多点大事给你愁成这样?哥问你,小贱胚子是几时入的赜兰居?”
说起那丫头他就来气,一个最低等的贱婢,能入他法眼,是瞧得起她。
倔蹄子居然不识好歹,梗脖子不从,当时给他脸上挠出好几道印儿,差点没把他子孙根踢报废。
要不是他一早备着软骨散,还成不了事儿。
珠翠:“差不离一个时辰。”
“这不就对了,赜兰居真要为那贱婢做主,早遣人来拿我了,可你瞧瞧外头风平浪静的,你搁哪儿自乱什么阵脚。”
旺才嗤笑道,
“不是哥说你,你呀耗子胆。”
“咱阿娘是大夫人院儿里的嬷嬷,你在老夫人跟前得脸,那位即便有心要问罪于我,是不是也得掂量掂量?”
不看僧面看佛面,她再是女君还能忤逆长辈不成?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有两座大山压阵,不明白他家妹子慌个什么劲儿。
“你啊,也别把那位太当回事,前些个族里府里大整顿,不过是新官上任,立威的虚把式,一个小娘子罢了,能有多大能耐,不定是个外强中干的主。”
旺才不耐烦挥挥手,
“赶紧回去当好你的差才是正经,且把心搁肚子里,你哥我出不了事。”
“唉,但愿吧,我说不过你,回了。”话虽如此,但珠翠隐隐有种不详的预感。
膳房采买管事旺才啊......这头裴姝听小青讲述完,不由挑了挑眉。
犹记得上一世,他是在秋节上犯的事,罪名是贪腐克扣,在外打着国公府名头强买豪夺。
底下的人犯了事,裴姝一贯实行一查到底,抖搂干净来个数罪并罚。
这一查可不得了,府里竟有数名丫鬟遭过他的荼毒祸害,其中有一位丫鬟因不堪受辱意图告发,被他残忍杀害抛尸沉在后院的湖里。
一经查明,裴姝当即下令杖二百。
由武夫行杖刑。
旺才养的细皮嫩肉,这二百打下去,就不可能再有喘气的机会。
裴姝就是要他死。
秦氏、老夫人轮番求情。
秦氏的要求就离谱,只准她撤旺才的职,不许她动用杖刑。
老夫人脑子稍微要灵醒些,折中杖一百,留他半条命撵出府去。
若不是考虑到几个丫鬟的名声,此等恶棍扭送官府,按照他犯下的累累罪行,依律判够他死几回的了。
秦氏如此拎不清,毫无是非观念,属实刷新了裴姝对她的观感。
那是上辈子的裴姝第一次不遗情面地违逆了两位长辈。
母女关系因此降至冰点,后面无论她怎么修复,秦氏也再没给过她一个好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