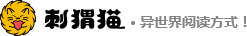谢显就不明白了,挺聪慧一个人,作起诗来,居然连基本的平仄韵脚都闹不明白。
前言不搭后语的叙事,凌乱的音节排序,不知所谓的意境,能把作古的诗圣们给气活过来。
听她吟诗一首,谢显遭罪得不行,只觉得一口气堵在心口,上不来下不去。
一时都分不清,让她作诗,究竟是在为难她还是在难为自己。
看他绷着脸,裴姝就知道肯定烂透了,架起的气势一泻千里,不免更加心虚了。
“应该还凑合吧?”
谢显忍住没发作:“你觉得呢?”
裴姝大言不惭道:“我觉着还行。”比之前在山上作那首水平高多了,可见还是有长进的。
谢显气笑了:“你可知,你作的诗能把读书人折磨死。”
尤其是对有强迫症的人特别不友好,批改都无从下手。
裴姝嘟囔:“折磨谁啦,不是你摁头让我作的吗。”
你活该,你自找。
谢显抬手压了压眉心:“你的鬼斧神工,你家尊师可知?”
“师父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裴姝毫无愧色地输出自己的观点,
“自认于诗画上略逊些,并无大碍。我不要求自己十全十美,人生苦短,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爱学就不学,没必要为难自己,舒心最重要。”
“只略逊了一些?”谢显眼角微微一抽,目光也沉了下来:“阿妤,你不是普通人,且担着太子讲义之责,面对自身缺陷非但不引咎自责,反倒找借口放任,你这是在自我放纵吗?”
终是忍不住了,他啪嗒把书撂案上。
声音格外响亮。
裴姝愕然一怔:“你在跟谁发火呢?”
有病吧。
是,上一世她就清楚地知道,谢显是一个相当严于律己的人,事事力求完美。
可她不是啊。
而且,他们什么关系啊?
屁关系没有,凭什么用他的尺度来要求自己,这不是有大病是什么。
谢显清隽的长眉不由蹙起,
“枉我好意提醒你要注意修正己身,你这般态度与帝京里不学无术顽劣成性的子弟有多大差别?”
萧启元呆萌茫然,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
还越说越来劲了,裴姝心里涌起一股不平的戾气,无论如何都难以压制。
她原本就不是什么好性儿的人,刺耳的话和他居高临下的态度,让她的忍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不是,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挨你训啊?本君一非你学生,二非你属下,你管我放纵不放纵,顽劣不顽劣。犯得着用你疾言厉色说教?”
“听我吟诗你难受,你遭罪,可那是本君逼你的吗?”
“没完没了了还,给你脸了是吧,你谁啊?”裴姝一鼓作气宣泄了出来,这里面不光有今天受的气,还有上一世处处被他压一头的憋屈。
殿内落针可闻。
四目相对。
死一般的寂静之后,谢显面上像一片波澜不惊的海面:“你说的对,是我自作多情自以为是了。”
他的平静只是一种表象,表象之下是山雨欲来的沉怒,裴姝嗅到了浓浓的危险的气味,寒气自脚底板往背脊骨上窜。
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才克制住没往后退。
事已至此,认怂也是枉然,该来的总会来,裴姝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此刻,谢显冷着脸坐在圈椅上,搭在椅背上的手指握得不由紧了那么两分,一瞬不瞬地凝视着裴姝。
他不笑时很吓人。
裴姝心里发怵,却是半步不退让,清凌凌直视着他。
看她严阵以待与自己对峙的模样,谢显眼底划过一抹轻嘲,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好笑,竟会因着一点微末小事与她置气。
“裴姝,我现在给你两个选项。”
他冷冷扯开唇角,嗓音冷硬直呼她全名,一字一顿道,
“你自认诗画略逊,作为同僚我建议你扬长避短总该是无错了。如此,殿下课业,你我对调。”
“选项二,诗可以不作,但殿下对丹青尤为感兴趣,所以,日后书画课你须与殿下一同听讲。”
强势如他能给人选择权,便是让步的体现,尽管不甚明了他为何突然就消了气,但傻子也知道,当下不能再火上浇油。
“我选后一个。”权衡利弊后,裴姝决定卖他一个面子,坚决不承认是怂了。
裴姝那句“你谁啊”,约摸是戳到他肺管子,千方百计也要给彼此扯上一点关系。
他就是这样,总有法子让你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
心中那股不平的戾气平息下来后,裴姝表情迷惘,搞不懂事情怎就演变成现今这个局面。
从给太子讲义,稀里糊涂变成了听讲的学生,想想就荒诞得很。
所幸,皇帝为了模糊大众视线,还从翰林院选了三位先生出来为太子传授课业。
再一个书画也不是主要课程,算下来平均五日受一遭罪,尚在忍受范围内。
插曲揭过,谢显与小太子讲了一篇《战国策》,从天禄阁走了出去。
外头日高三丈,他自暗处走向明处。
明亮光线将他高挺的身形衬托得神姿高彻。
直到看不见他人,萧启元才轻轻吐出一口气。
终究是他年幼无知了,本以为和善宽容的谢侍郎,竟比老学究们板着脸发火的样子还可怕。
小太子望着对面整理备课资料的裴姝,期期艾艾问:“先生,你是不是也很怕谢先生?”
“怎么会!”尚沉浸在表演中的裴姝咻地抬起头,严词否认:“嗐,他就会空口唬人罢了,你看他最后不也没把我怎样吗。”
“这样啊......”小太子犹犹豫豫道:“可我认为,谢先生凶你是不对的。那什么......你可不可以去跟父皇说,让他换一个先生。”
“不可以诶。”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拿别人当枪使,唆使她去皇帝面前打小报告。
算盘落空,小太子一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