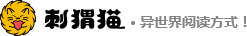坊间流出各种离谱的版本。
都传裴家女公子为着一个兔儿爷,连颜面都不要了。
常常漏夜出行,达旦欢畅。
什么一掷千金博郎君一笑,又说那郎君是个有骨气的,抵死不从。
笑谈裴家大抵是种不好,上一辈的老二如此,这一辈里也出了这么个货色,天要绝裴氏。
那些个闲得孵蛋的书生们批斥裴姝身为女子沉溺风月场所,伤风败俗,离经叛道;
身为女君不思进取,骄奢淫逸昏庸无能。
大放厥词将她与京中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做类比。
还有更荒诞的版本,说是裴府女君仗着身份,于狂风暴雨之夜逼上门,霸王硬上弓......
编得有声有色,细节详实,就跟站在床头亲眼瞧见了似的。
不对,有几回是没避着人,可夜里翻墙的事,天知地知除她们三个外,就赶马的厮役是个外人,芸雀激怒一拍掌,
“我知道源头在哪了,看我不去撕烂他的嘴。”
“站住。”裴姝把吃到一半的糕点扔回盘里,拍拍手上的碎屑,拿过茯苓水漱了漱口,满不在乎地笑笑:“我不避讳,自有用意。”
那夜的马夫,便是故意挑了一个裴钰的人。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胡编乱诌,无下限中伤贬低你!”芸雀愤怒的点在于,在姑娘大力整治下,竟还有不开眼的宵小胆敢行背主之事。
当然,最最最让她在意生气的是,她家姑娘,要颜有颜,要钱有钱,要背景有背景。
有身份有地位,用得着霸王硬上弓?
未免太侮辱人了!
瞧不起谁呢!
不能想,越想越火冒三丈。
芸鹭看眼浑不当回事的裴姝,道:“女君,我觉着芸雀说的对,再是有意为之,也烧得过旺了。”
“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风评一旦形成便极难扭转,不论您用意何在,我认为都实在没必要为此搭上清誉。”
此事芸鹭站芸雀,外头谣言铺天盖地,固然有女君的推波助澜,可霸王硬上弓属实难听了些。
相当于把姑娘跟那些个欺男霸女的下三流货色归为一类了。
“不烧旺点不行啊!”裴姝幽幽叹气:“风不风评的也不当饭吃。”
倘若不剑走偏锋,很快,就在明天,她又会如上一世一样,站到谢显的对立面,面临不斗也要斗的局面。
此外,她要把缩头龟钓出来。
她风评恶化,无所作为,裴坤良第一个坐不住。
不怕他动,就怕他不动,稳坐钓鱼台。
像前世那般,她在台前斗的头破血流,他悠哉龟缩在幕后渔翁得利。
而将裴钰算计在内,只是顺带手而已,能多坑一个算一个。
以伤及己身名誉来博弈,虽是下下策,但管用就成。
翌日。
侍官如约而至,来宣裴姝进宫。
裴姝回京不到四月,皇帝保持着一旬召见她一次的频率。
今次可得打起精神应对,这关系到未来的幸福生活。
绝不能再走老路,一脚踏进深渊,跟披着圣人皮的魔鬼斗得死去活来。
这一世,她的愿望很朴素,清算恩怨,坐拥金山,吃好喝好,活到九十九寿终就寝。
进宫面圣,须沐浴更衣,仪容整洁。
上妆完毕,裴姝挑了件鲛纱织金撒花裙,衣带坠环佩,珠钗满头晃耀。
华贵招摇。
马车里裴姝看似懒洋洋靠在大引枕上假寐,脑子却在高速运转。
跟皇帝相处,分寸感的拿捏半点轻忽不得。
隔靴挠痒不起效,过了又要招致皇帝厌恶。
界线稍没忖量好,就要引火烧身。
一炷香后,马车缓缓停靠宫门,裴姝下车,自西侧门而入。
宫门内几步之遥,一架歩辇已在此静候多时。
这份殊荣,前世裴姝泰然领受,而今世,她生怕踏错一步就走回老路,于是便有了一分惶然。
殊荣是一把双刃剑。
歩辇不紧不慢步入宫廷深处,御前大太监樊高忠亲自侯在阶前,看见裴姝,远远就迎了上来,将歩辇引离主干宫道。
裴姝扫一眼不远处檐牙高啄的宫殿,偏头相问:“樊公公,陛下不在紫宸殿?”
“近来暑热,陛下白日里都在清凉殿处理政务。”樊高忠向前快走一步,靠歩辇近了些才回话。
一个小小的举动便能看出他的亲近之意。
裴姝翻了翻六年前的记忆,今次皇帝确是在清凉殿召见的她,心遂安了下来。
接近清凉殿,四周的风变得凉爽,也更安静了。
莲花池的凉阁内,高大身影凭栏而立,身姿挺拔,犹如刀壁斧削。
莫名地,裴姝却在他峭拔的背影里读出了一种难言的孤寂。
已是不惑之年的皇帝转过身。
他玉冠束发,一袭玄色直裾衬出帝王的威严。
“臣女请陛下安,陛下万福金安。”裴姝螓首低垂,弯腰作礼。
萧尧手虚虚一抬:“阿妤免礼。”
相比起那位死敌,裴姝听着皇帝唤她阿妤就要顺耳得多。
毕竟是跟师父一辈的人,且与师父渊源深长,抛开他帝王的身份,也算半个长辈。
“来,坐。”萧尧指指玉石桌道:“上次封盘的棋,今日下完罢。”
裴姝很是愣了愣,对她来说,那盘断棋已有六年之久。
相隔两千多天的岁月里,与皇帝对弈到半途,皇帝断了棋去忙政务了,实在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
“你这记性可比你师父差远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帝王露出些许笑意,惯常轻拢的眉舒展着,打趣道。
“臣女自是拍马不及师父。”裴姝抬头莞尔一笑,与他四目相对。
皇帝五官深邃,剑眉星目,眉间虽是蕴着一股子恹恹之气,却也不难看出年轻时有一副好姿容。
她这一抬首,琳琅满目的珠钗轻轻晃动,流光溢彩的丽水紫磨金步摇之下是一张明媚的娇靥,想不被人注意都难。
萧尧眼底绽出一分分意外:“朕瞧着,你今次的装扮大不同以往。”
裴姝目中浮现一丝悱然,似略不好意思地扶了扶步摇,低头道:“都说女为悦己者容,想来臣女也不能免俗。”
“你与旁人不同,何以要随波逐流?”她做出这副小女儿情态,皇帝看在眼里,不由狠狠拢了拢眉。
舜华一生卓荦不羁,素有林下风范。
身为她唯一的爱徒,如此作派实在不堪入目。
有堕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