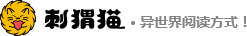一曲终。
裴姝击掌称绝:“沐公子不愧被誉为才色双绝。”
沐司翩然起身作揖:“女君谬赞,得幸近身侍奉贵人,诗书作文乃本等。”
“不才虽诗词歌赋略通,琴棋书画不精亦晓,却是愧不敢当才色双绝。”
“沐公子谦虚了。”裴姝抬起团扇往下压,做出一个阻止他施礼的姿势,下一刻却语出惊人:“据悉怀家三郎借住在你处,不知可否得你引见?”
怀三郎怀左,罪臣之后,曾出生官宦世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
沐司骇然抬首,无意之中不防直视了裴姝。
猝不及防地撞见一张天姿国色的容颜,使得沐司一时愣了一愣,随即浑身汗毛倒竖。
哪有什么慕名前往,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早年小生虽与怀三郎因琴结缘,然他在怀家获罪之后便不知所踪,何来在我此处一说?”沐司深深一长揖:“流言误人,还请女君明鉴。”
裴姝但笑不语。
芸鹭立即领会到该自己上场了:“放肆!女君岂是无的放矢之人。你是想被治个包庇罪,还是让女君承你一份情,烦请沐公子权衡之后好生答话。”
“嗐,这么严肃做什么,怪吓人的。”裴姝佯装轻斥芸鹭一句,对着神色惊异的沐司道:“你放宽心,我此次前来只有招贤纳士之心,断无恶意。”
“你视怀三郎为知己,当知他胸藏文墨怀若谷,你当真愿意看到他拘囿方寸了此残生?”
“岁聿云暮,日月其除,时不待人啊。空有才华却无施展之地实乃人生一大憾事,沐公子觉着这话可对?”
沐司目光里不由浮出几分异样来。
女君招徕之意已然溢于言表,这便不是他能做主的了,需由怀三郎自行决择。
他深思熟虑一番才道:“女君稍候。”
一盏茶后。
沐司回返,身后跟着位隽秀郎君,他姿容俊美,眉间隐然有一股书卷清气。
裴姝不待他站稳便出言相问:“怀三郎,本君后院夫郎位空悬,幕宾虚左以待,你当如何选?”
怀左拂衣行礼的动作一滞。
她摒弃虚礼问的急,似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怀左也应的巧妙:“女君启用一介罪臣之子,就不怕受牵累?”
据他所知,裴府这位女君远离京城十二载,回京不过三两月,根基尚不稳就敢大胆任用罪臣之子。
焉知她是自信过头,抑或是对周遭环境缺乏明确认知。
两者皆非好事。
裴姝坐在长案边慢慢吃着葡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既已在皇城脚下安然藏匿数年,说明天家对怀家并无赶尽杀绝之意,那便大有运作空间,端看运作之人能否有胆略,有魄力为之。”
“且当年那桩旧案并非全无疑点,只不过牵涉其中的权贵,怀家最势弱罢了。”
“当了替死鬼也说不准。”她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
裴姝说的云淡风轻,好似在评论果盘里的葡萄酸不酸一样。
怀左却被她的大胆言语惊得说不出话来。
心中亦是百感交集,自怀家获罪以来,除沐司为他抱屈喊冤外,她是第二个。
一旁的沐司也是一震,目光里是全然的不敢相信,她长年远离权利中心,何以对数年前的一桩旧案了如指掌?
尝过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滋味,怀左说不意动是假。
本朝制度,罪臣之后不得科举,他注定沉冤昭雪无门,起复无望矣。
大概率是要躲躲藏藏混吃等死,碌碌无为过完此生了。
而此刻......许是此生仅有一次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然,他又有所顾虑,她虽是身份尊贵的女君,可终归是一个女子。
他自小目睹父亲后院的妻妾们,整日就为着一点微末之事争得不可开交,丢弃人格尊严,卑微地只为乞求男人一丝怜爱。
与女子共事他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又基于不了解对方,缺乏信任。
须知女子多感性,易受情绪牵绊。
换而言之,无法掌控自我情绪,便难成大事。
怀左望着裴姝,一时不答。
男权社会,世人一贯将女性视作男人的附属品与陪衬品,大环境如此,心有疑虑很正常,裴姝并不催着他立时答复,
“你不必急着回复,后日我再来寻你,届时再答也不晚。”
话落,她抽出锦帕细致地擦着手,倏而抬眸,唇边含笑,兴致盎然地看着沐司说,
“这采南院,入目皆是风景,琴音更是如梦似幻,可谓是一杯弹一曲,不觉夜阑沉。韵味深长,闻之谐夙心。”
“葡萄也甚是甘甜,当得起流连忘返。”
忽如其来的一笑,恍若明珠生晕,美玉莹光,让人呼吸都为之一窒。
沐司失神一瞬,紧跟着眼皮狂跳,不愧是百年一遇的女君,性情颇有几分放诞不羁,于欲色一道,不比男儿逊色!
刹那就把气氛撩拨的旖旎起来。
裴家女君是何意?传闻她正在寻觅夫郎,莫不是看上他了?
不,休想,他是不会屈从的!
沐司在那儿一阵头脑风暴。
其实吧,他和怀左都被裴姝玩的这招避实就虚给绕进去了。
其实他也是裴姝的目标之一。
准确来说,沐司才是裴姝首要的目标人物。
五年前,禹杭河道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
落水坞坞主孟氏一族三百余口在一夜之间尽数葬身火海。
全族一夕覆灭,唯外出游学的孟家五郎,孟不凡侥幸逃过一劫。
也就是眼前的沐司。
诡异的是,这等重案惨案,朝廷对此却保持了高度的沉默,当地衙门也只是派人草草调查了事。
后续坞堡派众暗中遭到不明势力的清算。
有那耳聪目明的闻风而逃,接应上孟不凡后,行踪成谜。
流传他们逃去了域外,实则秘密潜入了帝京。
孟不凡入京后第一时间联络了户部侍郎怀危莆。
怀氏一族牵扯在内的饷银失窃案和孟氏灭门案看似两不相干,却属同一桩。
那离奇失踪的六百万官银,便是在禹杭附近的河道不翼而飞的。
有时候人一旦走起霉运来,坏事就凑堆的来,孟不凡这厢刚跟怀侍郎接上头,怀家就出事了。
仓惶紧促之下,孟不凡只得改头换面,栖身采南院以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