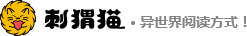深秋衰草凄凄,枯叶打着旋儿零落一地。
苔藓斑驳的偏僻废院突兀发出“咣当”一声响,陈旧木门不堪重负分崩离析,寒风涌入。
一位盛装打扮的小娘子提裙而入。
箪瓢陋室,顿显华光溢彩,与屋中人的黯淡形成鲜明对比。
裴姝乌黑眸子云淡风轻睨过去一眼,遂移开视线。
花容月貌的小娘子居高临下俯视着她,娇艳红唇发出胜利者志得意满的嗤嘲,
“阿姊连多看我一眼也不愿了吗?”
裴姝不语。
裴钰拢了拢狐皮斗篷,细白手腕晃动间,镶嵌在镯子上的红宝石灼出夺目光芒。
“也是,见着我岂不提醒着你,我们天资聪颖德才兼备的女君,竟败给华而不实的花瓶,多么讽刺。”
“也不知是世人有眼无珠,抑或是你名不副实。”
苍白枯瘦的年轻女子背脊挺直,跽坐蒲团,一双冻得生了疮,红肿溃烂的手安然放于膝上。
仪态一丝不苟。
眼神无波无澜。
输了就是输了,她无话可说。
裴钰恨透了她这副无论何时何地都宠辱不惊的模样。
明明已是众叛亲离,满盘皆输,不是应该崩溃,歇斯底里吗?
凭什么还能如此从容沉稳。
裴钰暗恨不已,几欲想挠花眼前这张波澜不惊的脸,
“成婚数载连个孩子都生不出,你呀当真不堪为妇。”她不知想到了什么,嘴角蓦然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
“多年来你在裴家当牛做马,苦心孤诣振兴家业,却无人感激你,国公府所有人啊恨不得你死,你说你的付出,像不像一个天大的笑话?”
满含恶意的话似风霜刀剑张牙舞爪扑来,裴姝既不悲愤,也不伤心,甚至有点想笑。
就觉着吧......面前这个视她如生死仇敌一般的妹妹骂的很对。
不可否认,她这一生确实像个笑话。
血脉至亲合起伙来欺她,骗她,利用她。
精挑细选的夫郎厌她,憎她,背弃她。
一個個无不企图踩踏着她的尸骨血泪往上爬。
裴姝不禁反省,她看起来就那般好欺负?
裴钰扯着嘴角,擎等着看她的好阿姊变脸。
结果自然是大失所望,几番激怒,对面的人始终平和如一,宛若一泓止水。
她单薄枯槁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某种巨大坚韧的力量,面对失败和即将到来的死亡,坦然而静远。
裴钰心生不甘,誓要把这张冰面皮撕下来不可,
“喜贺阿姊功成身退,你安心去吧。若有来世,阿姊可要吸取教训啊,万莫再揽权弄势,乖乖做回女子的本分。”
女子理当安安分分守在后宅相夫教子,而不是不自量力妄图执权。
一切皆是自身种下的因,怨不得旁人。
“你知道前姊夫,我的未来夫君如何评价你吗?他说你牝鸡司晨,豺狼成性,哈哈哈……招致枕边人厌恶至此,我都替你感到可悲可怜呢,阿姊你做人真是失败。”
打击宣泄一通,裴钰总算畅快了些,她冲着皇城方向,高高扬起下颌,
“阿姊,你快看那里,宫墙之内,阿耶他们今日发动了政变,裴家即将登顶至尊宝座。”
“哎,可惜你看不到了,裴氏一族的荣光于你再无关。”
始终神色淡淡的裴姝倏忽轻笑:“尔等得意忘形的过早。”
只要那个人在,裴家必不能如愿。
一声笑仿佛扯断那根强行压制的弦,绞痛排山倒海袭来,喉咙腥甜再也遏止不住,
黑红的血从唇角汹涌溢出,裴姝的思绪逐渐涣散。
前院隐约嘈杂。
神志被暗夜吞没的最后一瞬,裴姝听见有人惊慌失措疾呼,
“小娘子大事不好,神策军围了国公府……”
啧,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
不枉她与虎谋皮布局一场。
他们都以为她胸襟宽广,错,大错特错,她这人其实挺记仇的。
死......也要拉上几个人陪葬,不然黄泉路上多寂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