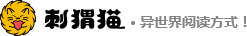李府的宅邸看着挺俭朴。
但再俭朴那也是宰辅家,宰辅之家不是公共厕所,不能想进就进,按规矩得先递拜帖。
马车到了李府门前停下,夏源坐在车上没急着下去,老王向着门房递上了名贴。
李府堂屋的偏寝之内,李东阳刚刚享受过药浴,又上了药,正光着腚半趴在榻上。
堂屋里传来一阵脚步声,走到门口就自然而然的停下步子,朝着寝屋唤道:“老爷。”
“老夫不是说不要打扰吗?”李东阳先是皱眉,旋即才问道:“何事?”
“府门外头有人递上拜帖,说是来拜访老爷的,名帖上写着东宫少詹事夏源。”
夏源?
李东阳一愣,这小子来做什么?
心里暗自揣测着,他扭头道:“先让兆藩去接待一下,老夫随后就来,记住,不可慢怠。”
“是。”
听到外头的人走了出去,李东阳伸手摸了摸后头,疼的一抽嘴角,药还没干,得等会儿。
坐在面前的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长得还算周正,李东阳的儿子,名叫李兆藩。
夏源盯着他瞧,李兆藩明显是个腼腆的性子,被瞧的有些不好意思,问道:“不知夏大人为何一直盯着在下看?”
“噢,没什么。”
夏源把目光挪开,捧着茶杯嘬起来。
李东阳的长相那是出了名的其貌不扬,而且这个其貌不扬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其实是丑。
但这个李兆藩却长得还算周正,并且不论是眉眼,鼻子,嘴巴都没有和李东阳相像的地方。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实在是让人怀疑这个李兆藩是个转基因产品,难道李家有传说中的爹保高速,或者妈厨高速?
当然,这种话不方便问,属实是太失礼了。
而且他来这里也不是问这个的。
“令尊大人何时才能出来?”
“怕是还要劳烦夏大人再等等,我父亲此时不方便见客。”
“不方便?为何不方便?”
李兆藩想了想,含糊其辞的道:“父亲在用药。”
“用药?令尊病了?”
“是有些病症,但不碍事,积年久症。”
见这李兆藩像是不想多说,夏源便没接着再问,何况他也大概猜到了。
当初在濮州时,给李东阳安排的工作虽说不体面,是个很清贵的库管,但起码是给配着椅子和书案的,毕竟是阁老,总不能让人站着。
但每次去的时候,总能瞧见李东阳在那儿站着拨算盘子。
有椅子不坐,偏要站着,这不是椅子上有钉子,就是屁股上有痔疮。
身怀大痣,还要为大明朝发光发热,实在是让人敬佩。
又等了片刻,李东阳终于踱进了前堂,夏源连忙起身,表情严肃的对着李东阳行礼。
“下官见过李阁老。”
李东阳穿着身宽松的袍服,像是道袍的款式,见夏源行礼,立刻加快步伐,走到近前用双手将他托起,“老夫方才被些许琐事耽误了些时间,倒是劳夏詹事久候,实在是失礼,老夫在此向你赔罪。”
“李阁老真是折煞下官了,万万担当不起。”
夏源表现的很有礼貌,李东阳表现的很热情,拉着他在椅子上坐下,“夏詹事此来,所为何事?”
“看望一下李阁老,顺道和您聊聊天,下官可是最敬仰李阁老的。”
对这话,李东阳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但脸上依然挂着和煦的笑容,“可是为了修路一事而来?”
“是也不是。”
“此话怎讲?”
说着,李东阳往旁边看了一眼,李兆藩会意,冲着两人行了个礼,然后便默默退了下去。
夏源没急着回答,反而问道:“李阁老,晚辈想向您赐教,您说这为官者,为臣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见他如此煞有介事的问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李东阳没有冒然回答,沉吟片刻才道:“忠君为国。”
“晚辈再赐教阁老,当是先忠君,还是先为国?”
这个问题无论怎么答都是错的,李东阳这次不接言了,只是望着他,片刻后,将问题抛回去,“夏詹事以为呢?”
夏源在心里整理着语言,嘴上慢慢的道:“依晚辈之见,若君王要做的事情于国有损,那便要予以劝谏;若于国有利之事,君王不肯去做,仍要予以劝谏;既是忠君,也是为国,没必要分出个主次。”
“而当一件事即是与国有利,君王又想要去做,那彼时臣子该做的应是领命去做,而不是反对,李阁老以为呢?”
“夏詹事觉得修路一事于国有利?”
“至少是利大于弊的。”
“夏詹事”李东阳这一声带着叹息,“便是再有利好,可国库无银,又如何去推行?夏詹事应当多想想国朝的情况,而不是脑子一拍就去做。”
“晚辈承认李阁老这话说得对。但晚辈觉得为官者,为臣者,最重要的是上匡社稷,下抚黎民。而为君分忧,为国分忧更是义不容辞之事,李阁老以为晚辈说的可对?”
李东阳沉默一会儿,颔首道:“对。”
“既然李阁老觉得晚辈说的对,那李阁老觉得何谓分忧?”
没等李东阳回话,夏源便自顾自的道:“国库无银,臣子该想的是如何让国库里有银子,这叫分忧。修路这件与国有利的事情推行不下去,臣子该想的是如何解决困难,将此事顺利的推行下去,这也叫分忧。”
“李阁老老成持重,凡事总有着种种考量,下官初出茅庐,论及思虑不及阁老万一。
但下官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世上无论任何事总有解决的法子,或易或难,若是觉得难就放弃,说一句此事做不了,就此作罢吧。
这不是分忧,这只是在退避,真正的分忧该是迎难而上,解决困难。”
李东阳的脸上没有了和煦,持之以凝重,紧盯着夏源的眼,“那夏詹事说说,如何解决这个困难?”
夏源没回话,而是反问道:“李阁老现下可有空闲?”
“老夫有。”
“那不知李阁老能否请出刘阁老与谢阁老?”
闻言,李东阳先是一愣,而后皱眉道:“你不止想说服老夫,还想说服刘公与谢公?”
“是。”
“老夫不善言辞,但谢公可是出了名的能言善辩,你怕是说不过他。”
“谢公是能言善辩,但晚辈只是想和他阐明道理,又不是要与谢公争论什么。”
李东阳深望着他,最后淡淡道:“也罢,老夫便遣人帮你去请他们。”
“不用这么麻烦,咱们顺路请上这两位阁老就好。”
“顺路?”
李东阳一怔,“你要带老夫去何处?”
“东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