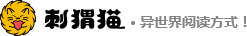帐中诸人面面相觑,不知道王远冲卖的什么关子。
进来的少年在座的大部分见过,是王远冲的幼子,唤作王智行。今年年初的时候才过了十二岁的小宴,在坐的便有人参加过。
王远冲的长子早夭,直到四十多岁才又有了这个幼子,那真的是宝贝的不得了。
“王大人,今日少公子有喜事?”邵振雄问道。
“智行啊,见过诸位长辈。”
王远冲并未答话,转头对自己的孩子说道,眼神中充满慈爱,也只有面对自己幼子的时候王远冲才不那么严肃。
“智行见过诸位叔伯!”
有礼有形,书香门第之家从小便带着一股子儒雅。
“好了,门口末尾的椅子坐那儿去。”
“孩儿谢父亲大人赐坐。”
一举一动有板有眼的,几个在场的老夫子不由得扶须点头,此子虽然年幼但却风度从容,若潜心研学未来定然可有所成。
王智行走到末尾端坐下,目不斜视,神情淡然不惊。
看着自己得孩子坐好之后王远冲方才走到主位旁。
邵振雄看着这一幕心里有种预感,或者说在场得人都有这种预感,这种情况大部分人都经历过。
果不其然,王远冲并未坐下,而是拿起桌上得酒樽说道:“诸位,请容老夫一言。”
场中很快变得安静下来,隐隐还能听到后院传来得啜泣。
“人生之乐有几何?金榜悬名乎?洞房花烛乎?久旱甘霖,他乡故知乎?此皆自乐也!良田阡陌成方,珠宝玉器满屋,珍馐美味果腹,此皆欲之使然,吾终难喜之。吾本建州村野,先父早亡,幸得朝廷资助宗族照料方得已苟存至今。又得祖宗庇佑侥幸中得一进士,为官十余载至大县父母官,也足矣。”
“圣人有云,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之,吾今年五十有三,为国为宗族者谋有何物?日夜思来实是有愧,故而吾为官不敢懈怠恐朝廷之恩蒙羞,不敢慢民恐百姓之恩折席,不敢不尊恐宗族之恩覆尘。”
“十余年来也算稍有心安。”
“若无意外老夫再过两年也该上书致仕,之后回宗祠为一守门人,至乡里为一夫子。”
“可靖人狼子野心,禽兽之军,竟无端犯我疆土戮我子民,使朝廷威严不存,百姓流离失所,所作所为罄竹难书,若不尽灭何以告慰百万生灵!”
“若无作为又有何面目面对乡梓面对朝廷,回了宗族岂还能有安息之地乎。”
“这十日以来我谷曲上下众心城城,即便暴雨狂风亦牢牢守得这百里河山,在此老夫拜谢诸位大义了。”
说完深深一礼。
在场得人对王远冲也是发自内心得钦佩,靖军围城之前是他顶着上官得巨大压力保住了辉州卫丁字营得最后两千战兵,靖军攻城期间又是他带头散尽家财,将府中所有得精壮派上城墙协守,连日来奔走调配,整个谷曲县数十万人被其安排得仅仅有条,没有饿过城上得将士一顿饭,缺过一口水。十天以来睡得觉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个时辰。
谷曲县得百姓看到他总是能感觉到心安,可以说眼前这个疲惫人父母官是靖人在看不到得地方最大得敌人之一,也是整个谷曲县老百姓心里真正得父母官。
“县尊使不得使不得啊!”
旁边得人急忙将其扶起来。
王远冲笑了笑说道:“老夫今日方才真正知道原来百无一用真的是书生,大敌当前老夫却不能亲自上城杀敌,不能和将士们并肩作战,生而有愧啊。”
这下邵振雄不能不说话了:“王大人何必如此自谦,若无王大人居中调度,这谷曲县哪里守得住十日。”
“邵将军说的极是啊,县尊大人,切莫再如此说了。”旁边的人附和道。
王远冲倒也洒脱说道:“好吧,那便不说这等矫情的话,这等小儿态老夫也是不熟练的很啊。”
见王远冲难得的自嘲了一次众人也跟着干笑了几声。
“智行啊上前来。”
王远冲右手搭在自己幼子的肩膀上,小家伙不苟言笑的样子倒是像极了王远冲平日。
众人也都静了下来。
王远冲扫视了一遍全场后说道:“老夫虽老提不动枪披不得甲,但有一子今已经初有长进,可代老夫上城助战。”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即便是没有反应过来的,即便少数几个庄赢这般起于微末贫寒之家的也明晓了。
这是父送子啊。
“王大人。”依旧是邵振雄开口:“如果本将没有记错的话令公子今年才十一吧。”
“虚岁十二。”
“王大人报国之心令人钦佩至极,可是令公子乃王大人独自,若出个意外当如何?王大人慎思。”
“况且本将还在用不着十一二岁的娃娃上战场。”
“若出意外自有我王家祠堂香火供奉。”
声从内院传来,中气十足,所有人不敢怠慢皆起身行礼。
“见过母亲。”
王智行也学着大人的样子躬身拜道:“孙儿见过奶奶。”
“王老夫人。”
王老太君走到正中央,看了一圈。
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邵振雄的身上。
“邵将军,老身还能说几句话吧。”
邵振雄连忙说道:“老夫人请讲。”
“那老身就谢过邵将军了。”
“不敢不敢。”
“这些日子以来靖人攻城每日死伤无数,老身都知道,每日里我王家众人大多在伤兵营里,或者在粥鹏里。老身虽然是一介女流之辈,可是也知晓家国大义,也知晓人伦之常。”
“邵将军,若老身没有记错的话整个丁字营进驻谷曲县的不到三千人对吧。”
邵振雄点点头。
“现在呢?阵亡已经超过两千,重伤无法上阵的也有小两百人吧。”
邵振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起来。
“本将还活着,还提的动刀,丁字营剩下的六百儿郎也提的动刀。”
嘶~~~
抽后槽牙的声音响起一片,很显然丁字营的伤亡超出了众人的想想。
王老太君说道:“城防营呢?老身记得留下来的有三千一百人差不多,现在还剩多少?”
“老太君这是想说什么?”
“邵将军不必紧张,今时今日,这谷曲县城什么情况你清楚,但是老身不见得比你差。”
“城防营三千一百多人,运下来的有两千六百多人,只有三百多人活了下来,能够重新上城的只有一百多人。”
“所以现在整个谷曲县的城上的披甲兵丁也就千人左右还得分散各处?”发问的是城中大户席家家主,席思年。
“可是下午我等运粮的时候分明看到披甲不止千人啊,城下藏兵洞内还有轮换兵丁也有不少披甲。”
王老太君太君说道:“大部分不过是民夫罢了。”
“啊!这!那这谷曲县还守得住么?”
众人听闻大惊,议论纷纷起来,心中的恐惧开始放大。
“王县令,你等这是要惑乱军心么?”邵振雄已经是很愤怒了。
“邵将军息怒,老身说了,不是那个意思。”
“那这是要做什么?况且这些数字你王老太君是怎么知道的。”邵振雄厉声问道。
“唉,邵将军,这些日子以来城中的杂事我儿哪一件都知道,他虽然从来没跟老身说过,可是连老身每日都在给伤兵包扎,都在洗药布,你觉得老身怎么知道的。”
“而且邵将军此等形态不正是坐实了?”
邵振雄心里一紧,果然场中诸人大部分神色异常,只是有自己在还能压着点。
“老夫人你不该!”
王老太君走到自己孙子旁边,慈爱的摸摸头,两人相互笑了笑。
“邵将军,老身相信邵将军和麾下的儿郎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也会挡在几十万谷曲百姓面前,死战不退,可是保家卫国不止是你丁字营的事儿更不是你邵将军的事儿。”
“带上来。”
两个下人抬着一具担架走了进来,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走到场中。
邵振雄三步并作两步的冲了过去,握着担架上的手紧张不语。
王老太君走到旁边说道:“我们的刘太守说邵将军把家眷送去了青城县,可是诸位来看看,担架上的少年叫谷之正,或者说叫邵之正,就是刘太守说的邵将军的三子,今年十六岁,也是永远十六岁了。”
邵振雄双手颤抖着摸着已经僵硬的手,抚过身上的刀痕,虎目含泪。
“邵将军,老身说了,这谷曲县的安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做的够多了,老身的儿子是谷曲县令,怎么也该我王家做点什么吧。”
“诸位。”王老太君走到场中说道:“诸位都知道老身我就这么一个孙子,我儿福薄,没有那多子多孙的命,但是靖人来了,烧杀抢掠,以我郑人百姓为两脚羊,每战必以我郑人之头祭旗,城外尸横遍野,四野荒芜,毁我家园,郑人者皆与其不共戴天。”
“所以今夜请大伙儿前来便是参加我孙儿的加冠礼!”
“啊?冠礼?”
“可是王老夫人,令孙虚岁才十二啊,二十弱冠,这是不是太早了?”
“邵将军之子十六,已经因为保护我谷曲安危阵亡,我孙儿十二如何不能加冠?”
“智行过来。”
“奶奶!”
“奶奶问你可知加冠为何?”
王智行一字一句的答道:“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属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衎衎于进德修业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内心不变,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所以成显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积,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
王老太君满意的点头:“很好,既然加冠便是成人君子,城上城中当有汝之热血。”
王智行肃然道:“必不敢以贪生为念。”
“好。我儿。”
王远冲急忙应道:“儿在。”
王老太君擦了擦眼角的泪沉声说道:“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