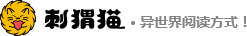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团率~”
牛大嗓门的声音让正在看舆图的张西阳抬起头来,一匹纯黑色的健马迎面而来,马上除了队正牛高之外还扛着一个人。
走到近前翻身下马,又把马背上的人一把捞下来:“团率,这是刚刚发现的一个断臂少年,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身上穿着一身皮甲,从南面来的。”
“南面?”
张西阳的目光迅速在舆图上扫过。
樟南郡!
此时张西阳等人已经是在青城县以南百余里的地方,五十余骑本来是想突围朝着正西去寻找援军,却没成想不到一日的功夫靖军已经在正西方向派遣了数万大军,把所有大小路堵的铁桶一般,张西阳等人不得已方才带着人马朝南行进,一方面探查樟南郡的情况,另一方面绕过敌军部队见机行事。
“把他救醒。”
牛高听闻早就含着嘴里的水直接就喷了上去。
“你干什么?”
“团率不是说弄醒么?标下一直也都是这么干的一喷就醒了。”
说话间少年微微的睁开了双眼,嘴里呢喃的发出一点声音。
牛高一乐道:“怎么样,醒了吧。”
“你那大嘴臭烘烘的,怕不是被熏醒的吧。”
众人闻言哈哈一笑。
少年缓了缓气,旁边有士兵地上水袋,大口喝了几口之后总算是感觉回过了一口气。
少年还是有些虚弱,看着众人问道:“你们是谁?是王师么?”
张西阳等人身上穿的盔甲分外威武,甲上的刀痕箭洞随处可见,一看便是经过大战的精锐之师。
还未等答话少年的眉头便紧皱了起来低头嗅了嗅不解的问道:“这是什么味儿?”
牛高老脸一红,周边军士的笑声突然就很放肆起来,让原本紧张的氛围有了一些轻松。
张西阳也是微微一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身上的皮甲和伤势怎么回事?”
少年扫视了一圈虽说心中已经有了肯定的答案但还是问道:“你们是大郑王师么?”
牛高总算找到了机会,蒲扇一般的大手拍在胸脯,肉掌与铁甲相撞发出清亮的声音,大脑袋一昂宛如斗架赢了的大公鸡骄傲的说道:“那是自然,我等是大郑肖州军,本官是肖州军重甲营甲旅二团二队队正牛高,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东宫卫率府队正兼任先锋团团率的张西阳张将军。”
说完还将身上的腰牌摘下来在少年眼前晃了晃。
一连串的名头砸的少年有些晕乎乎的,但是肖州军他还是很清楚的,身为郑国儿郎又有谁不知道肖州军呢,至于东宫卫率,那可是太子的嫡系人马,将来太子继位那前程不可估量。
但是少年眼中的欣喜很快便被悲痛所代替眼泪直接涌了出来:“肖州军,王师,你们真的是王师!你们怎么才来啊。”
说罢便扑倒张西阳的怀里大哭了起来。
众人面面相觑,有些不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众人见过了太多的家破人亡,眼前这个一眼看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想必所经历的也是难以承受的痛楚。
牛高脸上的嬉笑不见了,少年让他想起了那个埋葬了很多同族的万人坑。
靖人狼子野心又残暴至极简直不能称为人。
很快少年的哭声转为啜泣,或许是太累了又或许是突然之间有了安全感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功夫竟然就在张西阳的怀里睡着了,只是脸上挂满了压过的泪痕。
“团率,这……”
旁边一个士兵有些不知所措的问道。
张西阳也有些无奈,但还好只是一个少年,还在能力范围之内:“分出一匹马带上吧,先找一个比较隐蔽安全的地方再做打算。”
时间已经是六月上旬了,虽然整个大郑帝国境内夏天的气息已经很惹眼,但是在这辉州的夜晚却让张西阳等人感觉到一些阴寒,不知是否是错觉总觉得空气中有着淡淡的血腥味。
几个士兵出去猎了几只野物回来,众人在山洞中燃起火堆烤了起来。
这处山洞不仅偏僻而是地势低洼,洞口还隐蔽,最重要的山洞深处竟然还有地下水,只要烟雾不大便不需要担心什么。
没有佐料的烤肉除了一些焦味之外很难谈的上好吃但是少年还是被吸引了起来,拍一拍脑袋稍微清醒下便注意到了眼前的食物。
“饿坏了吧,来过来吃点。”牛高将一条兔腿撕了下来递了过去。
少年接过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即便嘴里塞的满满的还在继续咬,那凶狠的表情惹得众人一阵无言。
这个小家伙看着眉清目秀的,手上没有茧子想来定是大户人家的小少爷却给饿成了这副模样。
“给,喝点水。”
少年感激的看了一眼面前的大胡子,还真的是噎的难受,大口的水去,肚子里有了干货方才感觉这条命又重新回来了。
直到此时少年才开始认认真真的打量着眼前的这些人。
每一个人脸上或悲伤或好奇,洞口附近有负责放哨的士兵,接着火光还能看到背后的甲衣上错落的痕迹,旁边围坐着十几个人,其余的正在擦拭着刀枪盔甲,有的甚至打起呼噜睡得正是香甜。
少年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睛又开始湿润。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抬起头,他记得这个人,那个长得很凶狠嘴巴很臭的队正说过这个人是他们的团率。
“我叫王智行。”
声音还有点点沙哑,但是少年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下来。
“名字不错,多大了?”
“十二岁。”
“哦还是个小娃娃。”牛高的大嗓门又响了起来,砂纸一样的巴掌轻轻搭在了少年的肩膀上。
谁知少年也转过头恶狠狠的说道:“我不是小娃娃,我已经加冠了,是大人了。”
“哈哈哈哈哈。”
“你这小娃娃,哪里有十二岁便加冠的,最早也得十六岁,你看我们团率,今年十七,去年在军中加冠的。”这次说话的是朱贵。
少年眼中朦胧,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有了波动:“是我爹给我加冠的,当时朱老夫子和邵将军他们都在,还有张指挥使,周旅率,他们都在。”说着说着声音中已经带上了哭腔。
几人对视一眼都感觉到不简单,出于直觉都感觉到其中定然有隐情。
“王小兄弟,你先别哭,你先跟我们说说,你爹是谁,你刚刚说的邵将军张指挥使他们又是谁,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身上的伤和皮甲是怎么回事。”
“慢慢说,一个一个来。”
少年啜泣了好一会儿方才停了下来,手里还握着啃完的兔腿骨头。
“我叫王智行,家父是樟南郡谷曲县县令王远冲。”
轰!
少年的第一句话就是劲爆消息。
竟然是樟南郡谷曲县县令的公子。
谷曲县是樟南郡郡治,而谷曲县令的儿子孤身在这里,还断了一条胳膊,那谷曲县此时又如何了?
猪都不用想都能猜出来。
果然,少年继续说道:“前端时间靖军十几万大军来袭,刘盼之那个恶人身为太守不仅不思虑怎么报效国家安排城防反而在靖人还没到的时候便要带着城防营的人跑,家父和邵将军前去劝说,郡尉马步为虎作伥甚至想调集兵马围杀我父亲和邵将军,好在邵将军有备而去,才没有酿成仇者快的事情。”
“然后靖人来了之后家父和邵将军为了确保万众一心便只允许刘盼之带了少量心腹,剩下的所有城防营和辉州卫的将士们上城作战,家父则在城中调配粮草器械动员青壮。”
“可是靖军真的太多了,我们战兵才两千出头,加上青壮也不够三千,整个谷曲县的老百姓不管男女老幼都拼了命,大家都知道靖人残暴,若是城破了后果不堪设想。”
“十几万靖人啊,我不记得守了多少天,但是每天都从城下抬下来好多好多的人。”
“后来实在没有人了就半大小伙子上,也就是那时候家父提议给我加冠,加冠了就是大人,是大人就得出力去守城,我奶奶也说好儿郎在这种时候就是要去死的,我爹是谷曲父母官,我是他儿子那更得去死,否则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
“晚上给我加冠,邵将军来了,张指挥使也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张指挥使是被人抬着进来的,还有周旅率和宋旅率,还有朱老夫子。”
“那天晚上很热闹,然后我就是大人了,可以着甲佩剑了。”
“第二天靖军跟发了疯一样的攻城,我们没有箭,没有石头,拆了好多民房,到最后我们甚至把袍泽的尸体也当滚木扔了下去,那一天我亲手杀了一个,可是我也少了一条胳膊。”
众人听着入神,从少年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后面都是鲜血,张西阳仿佛看到了谷曲城头的厮杀,城墙上辉州卫将士和城内的青壮相互交错相互配合同仇敌忾的抵抗这靖人的攻击,不时有人惨叫着倒下,后方的人则立马补了上去。
鲜血顺着台阶和墙缝流了下去,沉浸在了泥土里。
耳边仿佛有厮杀声响起还有在肆虐中不甘的怒吼。
原先睡觉的士兵不知何时也坐了起来,静静的听着,身为军人能听到这种事情让每一个在场士卒的心里都分外的难受。
战士的荣耀来自于沙场,执长戈擒敌酋问罪于君前。
大郑三百年,除了最开始的那几年之外有何曾在自己的国土上抗击过敌兵呢?
这些年来大郑兵峰的盛名已经不复从前了。
这是耻辱!只能用鲜血才能冲淡的耻辱!
执勤的士兵呼吸有些沉重,或者说所有人的呼吸都很沉重,有一股火焰在压抑中慢慢的升腾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