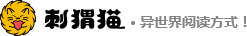祥符四年,正月十四。
楚识夏手心里闷了一层热汗,她看着棋盘上惨淡的战局,难堪地承认,“我输了。”
黑子一改之前老练沉稳的模样,将白子尽数绞杀殆尽,锋芒毕露。楚识夏持的白子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已然到了绝处,只能投子认负。
楚明彦却按住了她的手,“知道这种时候,怎么样你才能赢吗?”
楚识夏认认真真地再看了一遍棋盘,求知若渴道,“怎么样才能赢?”
楚明彦伸手按住棋盘边缘,猛地掀翻了棋盘。黑白棋子叮叮当当地打在地上,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声音经久不绝。楚明彦浅色的瞳仁像是映照着一线磨得光亮的剑刃,光芒冷冽。
“这是我教你的最后一个道理,长乐。”楚明彦淡淡地说,“这样你就赢了。”
“长乐……受教。”
楚明彦有些出神地看着她认真的脸,忽然笑了起来。楚明彦很少露出这样轻松的、不设防备的笑容,甚至有几分轻快,看得楚识夏有些呆。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教你这些。”楚明彦摇摇头,“当真是造化弄人。长乐,陪哥哥去看看父亲吧。”
——
楚识夏对父亲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高竖祠堂之上的灵位,数不胜数的军功。但她印象更深的是父亲的女人,环肥燕瘦、争奇斗艳。
那些姨娘们有的腰肢柔软,有的媚眼如丝,很难想象苦寒的云中会有这么多的美人。她们是这镇北王府里最华美的装饰,把死寂的宅子妆点得流光溢彩。
老镇北王是个合格的将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老王妃生下楚识夏后难产去世,楚明彦也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身体羸弱,要安抚惊魂未定的弟弟,还要照料襁褓中的妹妹。他生来就要保护许多人,成为许多人的依靠。
“识夏”这个名字是当时最受老镇北王宠爱的姨娘起的,那是个身怀异香的美人,笑或不笑都自有风情。老镇北王在外征战,楚识夏就被扔在王府里由她照料。
“这些日子我总是在想,我和长安应该早一点杀了那个女人。”
祠堂里,楚明彦取了一盏烛火,和楚识夏并肩坐在檐下。那么一点光,根本照不透眼前深邃的雪夜。
“香姨娘吗?”楚识夏摇摇头,“其实我都不记得她的样子了。”
香姨娘死于楚识夏五岁那年。
那年流民暴乱,香姨娘故意在逃亡路上扔下了楚识夏。楚明彦和楚明修违抗行军令,在难民群里四处寻找,才把差点沦为难民盘中餐的楚识夏救回来。
回到王府,楚明彦当众跑马拖死了香姨娘的一对儿女,冷眼看她哭得死去活来,才一剑杀了她。
“你知道她为什么给你取名‘识夏’吗?”楚明彦的声音有些冷,“‘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她要你做朝生暮死的蝼蚁。她盼着你早死,好让她的女儿取代你的位置。这些天我总在想,是不是这个名字就注定了你有离开我们庇护的一天?”
“哥,”楚识夏一把攥住了哥哥震颤不止的手腕,坚定有力道,“我会长命百岁的,你也是。这绝对不会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年。”
“长乐,你为什么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呢,”楚明彦有些苦涩,“是哥哥没有把你保护好吗?”
楚明彦和楚明修是鹰,却是被困死在边关的鹰。楚识夏身上寄托了他们得不到的所有东西,独一份的偏心、没有保留的爱意、随心所欲的自由。
她是他们的妹妹,也是他们看遍世间的双瞳。
“因为我很害怕失去你们,”楚识夏捧着他的手,轻轻地把侧脸贴上去,轻声说,“远远超过你们害怕失去我。哥,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恐惧。”
我生怕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我已是冢中枯骨,身旁躺着你和二哥。这云中再下一次的雪,不过将死之人的一场幻梦。
那种孤身一人在这世上的日子,我在也不要过哪怕一天。
我熬不下去的。
——
正月十五。
楚识夏的衣袖底下藏着佛珠,里三层外三层地穿了生青色的夹袄长裙,肩上披着白狐裘。她在祷告声中跪在蒲团上,巫祝的手指蘸着清水洒在她的额头上。
远行之前祭拜祖先,祖先便会保佑异乡的孩子。
祠堂外守候着楚家零星几个族老。
“长乐,你已经十五岁了,早该取字。今日你就要离家,此事不该再耽误。”楚明彦站在她身侧,朗声道,“长兄如父,如今我便为你取字‘墨雪’。”
伴随着“楚识夏”这个名字的恶毒诅咒灰飞烟灭,兄长赐她“雪”字,全了她的冬夏。
不求其他,只求她平安无虞。
“墨雪,谢过长兄。”
——
镇北王府外,车马都已经备好。
使团的宦官、书生们都恭谨地等候在车下,中间不伦不类地夹着一个带刀的男人。
黑色的甲兵们枪尖林立如云,楚明修骑着青骓缓缓从长街尽头走来。
楚明修上战场之前也是云中出名的风流少年郎,只是近些年杀气愈发的重,才惹得无人敢看他罢了。青骓小跑着穿过士兵们让出的路,楚明修身形恣意潇洒。
他勒马停在车辇旁,状似无意地问守在车旁的玉珠,“那些人就是帝都来的走狗?”
玉珠拘谨地点了下头。
恰逢使团里的梁先生和楚明修打招呼,楚明修笑得春风和煦地对他拱了下手,转过头笑眯眯地轻声和玉珠说:“真想杀了他们啊。”
使团里那个抱着刀的男人皱了皱眉,抬眼和楚明修对视。楚明修浑不在意地看了回去,唇边笑意不减。
玉珠端庄的笑容差点裂开。
楚明修十四岁就在军营里摸爬滚打,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块巴掌大的好皮。他说要杀谁,就一定不会让这个人活到第二天天亮,比如香姨娘,比如他那一院子居心叵测的庶弟。
算命的说楚识夏八字带煞,玉珠却觉得二公子的杀气比楚识夏重太多了。
玉珠心有惴惴时,楚明彦领着楚识夏出来了。
“长乐,二哥有军务在身,不能送你到帝都,只能送你出云中。”楚明修笑着说,“你别生二哥的气,二哥有好东西给你。”
“好东西我见的多了,二哥要给我什么?”楚识夏歪头,微微一笑。
楚明修摘下马鞍上挂着的长剑,远远地抛过去。
楚识夏抬手接住,触手生寒——剑鞘用黑色的鲨鱼皮紧紧包裹,对着日光隐约可见其上细微的纹路。她拔剑出鞘三寸,剑光清寒,露出剑镡上刻着的三枚古字“饮涧雪”。
“云中民风如此,望各位来使转告帝都的贵人,莫要把舍妹聊寄思乡之情的小玩意儿收走。”楚明修在马背上微微躬身,“楚明修在此深谢。”
一群使者脸色发白,敢怒不敢言。
楚识夏看得想笑,用力憋住了。
楚明彦轻轻地在她的后背上拍了一巴掌,像是拂去她衣上的雪尘,轻声道,“去吧。”
去吧,长乐,莫要回头。
若你回首一次,兄长就要心生不忍了。
漆黑的甲兵中间,红色的旗帜飘扬。楚识夏像是这堆被白雪覆盖的黑铁中长出的一根嫩芽,一步一步登上了车辇。楚明彦看着她的背影,楚明修俯视她的侧脸,所有人都在看她。
可她没有回头。
一次都没有。
楚明彦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感到难以呼吸。
“送大小姐!”
不知谁喊了一声,随即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镇北王府前。
“恭送大小姐!”
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远赴帝都,换取帝都对边关的信任,于这些战场厮杀的将士们而言,是一种侮辱。然而他们别无选择,甚至连镇北王本人都没得选。
楚识夏坐在车辇里,握紧了饮涧雪。
“走吧。”楚识夏低声道,“再晚走一步,我怕我就走不了了。”
——
护国寺的禅房外,梦机方丈来回踱步,挠着油光水滑的脑袋,犹豫再三才去敲了敲房门。
“沉舟,大小姐的车架已经出城了,你还在和她怄气么?”梦机方丈有些为难道,“去不去倒是随你,可你要是后悔了,恐怕后面追不上。”
后悔是一定会后悔的,要是追不上,难免又要找别的什么人的麻烦。
沉舟充耳不闻,坐在桌案前把拆开的信一封封折起来。
这些信并没有通过驿馆,而是有人从墙的那头扔进来的,有几封甚至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塞在枕头底下的。
信上写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见闻,五湖四海的怪谈、中原关外的风物,有的信纸背后还画着巍峨的拥雪关、草原上连绵起伏如云的羊背、江南细雨中的孤舟。
写信的人想必是不爱看书,措辞多半是从书上抄来的,遣词造句也并不优雅含蓄,透着直白的笨拙。
沉舟都能想象她捏着笔抓耳挠腮的样子——你看,这里也很好玩,那里也很漂亮,这个世界很好很大,你不是一定要跟着我去帝都,如果可以的话,也不要再生我的气。
沉舟被气得笑出了声,折好最后一封信塞进怀里,夺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