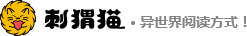沉舟只觉得自己全身陷进了黑色的泥潭中,楚识夏手上温暖柔软的触觉、楚识夏恍若隔着海水传来的声音、楚识夏渡到他唇齿间的血,一切都模模糊糊的。
别哭了。沉舟想说。
有什么好哭的呢?刺客都是要死的。
能死在你的怀里,能有人为我的死流眼泪。沉舟不自觉地想笑,也许我是所有死于灼心的刺客里,最幸运的那一个。
可是楚识夏的眼泪掉到沉舟的脸上,像是一滴滚烫的铁水,烫得沉舟的皮肤灼烧般的疼,一直疼到那颗冷冰冰的心脏里,叫它不得不震颤着跳动。
别哭了,沉舟想说,以后会有别的人替我守着你,在每个寂静的月夜行走在你的屋脊上;会有别的人握着刀剑替你杀人,掠夺你想要的一切;会有别的人抱你……吻你。
他会比我,更懂你为什么哭、为什么笑。
那个人会不会像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书上写的那样,同你赌书泼茶,同你当垆卖酒,同你在庭中种一棵枇杷树?
那个时候,你还会想起,你曾经为我哭过吗?
沉舟很想要落泪,他分明不懂什么叫悲伤,只是觉得心口隐隐作痛。
我很想那个人是我,可这条命,是我祈求神明要付出的代价。
沉舟在黑暗里想象楚识夏的泪眼,透明温热的泪水,湿漉漉的睫毛,湿润的瞳。
他想抬手为她擦掉眼泪,学着王府中的三花猫一样,摸摸她的头,却不能了。
没有关系。沉舟想对她说,从我不能说话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要付给神明的报酬。
但我不后悔。
你不要怕啊,沉舟无声地说。
这一次,神站在你这一边。
——
前世,祥符十三年。
沉舟折返回拥雪关的路上,遇到了无数拖家带口奔逃的流民。
一家人或是抱着小小的包袱,或是赶着驴车。在脸上涂抹泥土的女子、在怀中揣着菜刀的男人、被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每个人都在往南逃,求生。
只有沉舟向北走,那里尸山血海、流血漂橹,只有那里才有他的生路。
“拥雪关破了,北狄人打进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流亡的百姓们顿时骚乱起来。
沉舟猛地勒马,寻找喊出声的人,却看见三两个北狄人策马而来,他们的兽皮铠甲上血迹未干,手上的大刀收割稻草般对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头上砍去。
“咻”的一声,一枚羽箭正中北狄人眉心,白羽震颤不休。
那人缓缓倒下,女人抱着孩子连滚带爬地跑远了。沉舟放下勾弦的手指,冷冷地看向挥舞着铜盾和刀冲过来的北狄人。
北狄人以骑兵见长,根本没把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公子放在眼里。
但沉舟倏地从马鞍上腾起,没有重量似的踩在铜盾上,剑锋以刁钻狠辣的角度刺进北狄人的咽喉。另一人挥动长刀拦腰斩过来,沉舟一脚踢在死去的北狄人头颅上,那一刀劈进同伴的肩胛骨里,未等他将刀拔出,剑锋便穿透了他的心肺。
白雪皑皑,鲜血如火。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百姓们痛哭流涕,沉舟却心乱如麻。
“拥雪关……已经破了么?”沉舟抓过一个人,眼角发红,“那楚家大小姐呢?”
拥雪关全军覆没。
没有粮草、没有药材、没有援军的拥雪关驻军被数倍于自己的北狄军队围歼,却也拼死一击,消磨了北狄军队的主力精锐,为阕北四州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北狄大军不日自北方开拔,即将卷土重来。
消息传回青州的那一日,沉舟终于抵达了死气沉沉的拥雪关。
白色的雪、黑色的城被鲜血浸染,楚氏王旗插在城头,随风哗然。一层又一层的大雪仍然覆盖不完堆积如山的尸身,枭鸟啄食着尸体,猝不及防地被来人惊动。
沉舟茫然地行走在腥气冲天的拥雪关内,良久,才动手用剑鞘刨开雪尘,一具又一具尸体地翻找起来。
七天七夜,他没能把整个战场的尸体翻找出来,也没能找到楚识夏的尸身。
战场上刀剑无眼,生死平等地从每个人身上碾过去,不会因为她是拥雪关的将领、是被褫夺封号的镇北王而手下留情。
筋疲力尽的沉舟靠在雪堆上,望着灰蒙蒙的风雪,忽然抬手在自己湿润的脸上摸了一把——温热的,不是雪水,是他不知何时流下的眼泪。
“沉舟,回去吧。”
沉舟猛地睁开眼睛,眼前空无一人。
“沉舟,你要……好好活下去啊。”
那个缥缈又悲伤的声音说。
然而他的眼前,只有风雪拂过。
——
沉舟最终还是找到了楚识夏唯一的遗物,被她藏在拥雪关主将营帐中的佛珠。这串为主人挡过箭矢的佛珠早已伤痕累累,沉舟要带它回云中,为楚识夏立衣冠冢。
尘归尘,土归土。
死人的事完了,沉舟再去算活人的账。
可云中,早已不是当初的云中。
城中百姓聚集在昔日的镇北王府外,群情激愤、声浪如潮。王府门前驻守的是佩戴着皇家纹饰的羽林军,面对百姓扔来的石头和烂菜叶狼狈不堪,立刻就要拔刀动手。
沉舟一人一马出现在人前,生生按着那名羽林卫的手,将刀摁回鞘中。
“来者何人?”羽林卫憋红了脸,却无法从他手中挣脱分毫。
“楚家大小姐的未亡人。”沉舟冷冷道,“你们又是什么东西,也敢鸠占鹊巢?”
“楚家早已被削去爵位,楚识夏不仅不进京待罪,还擅自拥兵不出,意图谋反。”羽林卫愤愤道,“你是她的未亡人,难道也要犯上作乱吗?楚家果然辈出乱臣贼子!”
“你胡说!”
“一定是有奸臣冤枉大小姐,绝不可能是这样!”
“楚家就这么一个孤女,死在了拥雪关,你们帝都的大人物不要太过分!”
沉舟还没开口,门前的百姓怒吼出声。
“楚家满门忠烈,镇北王为了阕北四州殚精竭虑,楚家大小姐死守拥雪关,怎容你等小人诋毁!”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撸起袖子就要扑上来饱以老拳,却被沉舟轻轻巧巧地反手推回了人群中。
不待羽林卫得意,沉舟忽地暴起,剑鞘不偏不倚地抽在羽林卫腮边,直肿起两只高来。羽林卫被揍得七荤八素、眼冒金星,剑鞘又霸道地捅进他口中,捣碎了他满嘴的牙。
沉舟一脚踹在他胸口,人飞出去砸在石狮子上,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剩下的羽林卫们都惊呆了,一时间竟然不敢动作。他们奉命护送钦差大臣到这里,路途上阕北的硬骨头们一反传闻中的凶神恶煞,对他们毕恭毕敬,这还是第一次踢到铁板。
“让开,”沉舟淡声道,“这不是你们能进的地方。”
羽林卫们不得不拔刀应对,却被他一个人逼得步步后退。
“公子……”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形冲破了层层包围的羽林卫,扑到沉舟身前,抓着他的衣角痛哭流涕,“沉舟少爷,你快去看看吧,瑞王要烧楚家的祠堂!”
沉舟勉强辨认出这人是王府里的护卫,他浑身上下都是伤口,小腿骨以一个扭曲的姿势拖在身后,不知道是怎么跑到这里的。
“瑞王?”
钦差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先帝的三皇子,新帝一母同胞的弟弟,新敕封的瑞王。
白煜。
——
楚家祠堂前种着一片梅树,每年深冬,楚识夏都会被拎到此处祭扫。
沉舟无名无分,本没有资格进楚家的祠堂,但楚明彦每每都牵着两个小团子来。后来两个人犯错,楚明彦也一视同仁地让他们到这里跪着抄家规,抄完了就现编一百条不重样的,接着抄。
是以,沉舟对这里非常熟悉。
火光映雪,梅树和祠堂都被付之一炬,泡在汪洋火海中。
这样大的火,像是要连同整片天幕都烧掉,却点不亮沉舟的眼瞳分毫。
娃娃脸的年轻人坐在大火前的太师椅上,脚下踩着昂贵的雪貂皮,指间转着一枚翠莹莹的翡翠环。他看上去才二十岁出头,眼睛圆圆的,像小猫小狗般可爱,却有一种天真的残忍。
“又来了一个。”瑞王轻蔑地说,“你就是楚识夏的未亡人?”
沉舟眼角一斜,视线落在被羽林卫扭着胳膊按着跪下的人身上。玉珠身上的罗裙被血浸透了,鬓发散乱,眼神却冷漠而疯狂。她看向沉舟,却没有求救。
“这侍女倒是杀了我不少人。”瑞王笑起来,“楚识夏死了,楚家竟然一个能问罪的都没有。好在还有你们两个可以交差。”
“火是你放的?”沉舟的声音云淡风轻,却饱含杀意。
“是本王放的又如何?”瑞王嘲弄道,“本王不仅放了火,还砸了楚明彦和楚明修的牌位。楚识夏拒不入京认罪伏法,又兵败拥雪关,教出这样的妹妹,他们也配开宗立祠?”
“拥雪关兵败,是因皇帝执意问楚家莫须有之罪,断粮断援兵。”沉舟不带一丝感情地阐述事实,“昏君教出你这样的弟弟,你们俩都该死。”
瑞王脸色骤变,拍着太师椅吼道,“你这个乱臣贼子!给本王拿下,押送帝都剁了喂狗!”
最后一个字还未飘散在风中,沉舟先发制人,杀手剑从鞘中游鱼般滑出,雪光泼溅。
一拥而上的羽林卫转眼间便分崩离析,大多数人都只是感觉喉间或心口一冷一热,随即失去了力气。没人能看清沉舟是如何出剑的,只能看见零星划出的银光,搅碎了迸溅的血色。
他出剑很少,但每一剑都是必杀。
亲卫见状不对,连忙护着瑞王逃跑。
但为时已晚,沉舟袖底飞出一枚袖箭,直没入护卫心口。摔倒的护卫撞到了瑞王,盛气凌人的小王爷狼狈地坐在地上往后退。
“你敢杀我?我哥哥可是皇帝!他会诛了你的九族!”瑞王色厉内荏道。
“我杀的就是皇帝。”沉舟冷漠地欣赏着他难以掩饰的恐惧,像是酒鬼终又尝到了美酒。
沉舟一剑刺进他的膝盖下,一点点挑开骨下的筋肉。瑞王发出非人的惨叫,竭尽全力地往前爬,在雪地里留下一串血印。沉舟挑得他翻过身,剜下了他的髌骨。
“啊!”瑞王尖叫着,双手深深地扣进雪地里,“你敢!你敢!你这个乱臣贼子!”
沉舟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拎回祠堂前,要以他的骨、他的血和他的项上人头做祭奠。
“我没有九族给你诛,除非九泉之下,也是你的皇帝哥哥做主。”
“乱臣贼子?我做你的臣子,你也配么?”
“除了姓楚的之外,今天不会有一个活人能走出这里。”
沉舟一字一句,清晰有力。
沉舟话语里的每个字都透着血淋淋的杀机,这么多年,玉珠从未听过他一次说这么多话。楚识夏曾说沉舟是个心很深的人,他的喜怒哀乐都埋得很深很深,深到他自己都察觉不到。
现在,那些深埋的恨和怒喷薄而出,要如铁流般席卷过所有毁掉楚家的人。
瑞王除头颅外的每一根骨头都被沉舟拆了出来,这样的事他做来竟也得心应手,没有一刀是多余的。
人头、骨骼和皮肉都被沉舟扔进了未熄的火海。
“沉舟,你把大小姐带回来了么?”玉珠靠着梅树,虚弱地问。
沉舟侧立在火海前,沉默地摇摇头。
玉珠终于哭出了声,哭得手脚发软,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你不是说,你一生都守着她吗……”
玉珠湮灭在哭声中的后半句未竟之言,沉舟竟然无师自通地听懂了。
你不是说,你一生都守着她吗?她死了,你连她的尸身都带不回来了,你又回来做什么?
沉舟仰头看着天空中飘落的雪,满天的雪像是都要落进他的眼中,就此埋葬他的一生。
是啊,沉舟想,我还回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