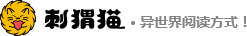余杭县的人家很多,家家户户也都挂着门号,白玉京很方便地找到了这家姓邢的人家。
府门外挂着白绫,里面的灵堂还没有撤走,死者还未入土。
今日已没有吊唁的人了,只剩家里的一对母女在灵堂前烧纸。
秋风萧瑟,即便是艳阳高照,都没有将这片肃杀洗净。
白玉京登门,府门里的管家立刻迎了出来,看白玉京穿着便明白不是寻常百姓,当即拱手问道:“阁下是?”
白玉京道:“我来找邢掌柜。”
这家主人姓邢,单名望,在余杭县秋叶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也算是有些家业,才置办了这坐宅子,女儿邢月娥芳年十七岁,长相出众,更是才气非凡,是十里八乡都闻名的才女。
管家自当引路。
白玉京路过那灵堂时看到了一个妇人在旁啜泣,还有一个小丫头同样穿着孝袍,跪在地上往火盆里丢纸钱,她还不到明辨生死的年纪,只觉得好玩,脸上还带着笑意,轻声道:“姐姐,姐姐,娘说多给你些银子花。”
入正厅堂,进侧屋,进了书房,白玉京看到了一个正在写字的人,此人正是邢掌柜。
奉茶之后,房间里就剩下了白玉京和邢掌柜。
邢掌柜估摸也就是四十左右的年纪,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脸上也不见颓色,坐在白玉京面前,恭敬道:“公子,您是县尉大人的门客,来此是想问小女的事情吧?”
白玉京点点头,“不错。”
邢望摇头丧气道:“当日县尉大人来了之后,我便将一切能说的都说了,这几日又回想了一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白玉京道:“不知可否去邢姑娘的屋子里看一看?”
邢望道:“当然可以,大人请。”
这间屋子的采光并不是很好,在整个院落里最角落的位置,倾斜的日光照射进来,映出空气中的粉尘,汇合着一股淡雅的香气,包裹着刚刚进门的白玉京。
邢望站在门口低声道:“大人请便吧,我在外面等您,就不进去了,以免睹物思人。”
白玉京没多说什么,走进房中。
少女的闺房总是神秘的,白玉京也没有想过自己第一次进入闺房时,与那少女早已阴阳两隔,一番探查下来,私密之物倒也没有多少,确实也没什么更多的发现,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
他闭上了眼睛,运转九曜星宫,将玄武二星穴调转至首位激活,登时他的身体仿佛不能动弹了,可在这一刻,他隐隐感觉到了周围某个地方有一个暗暗的气息,这个气息散发出来的,便是之前被体内的猪吃下去的黑雾。
目光转向床头的那一刻,体内的猪也苏醒了过来,哼唧了几声,伸出舌头围绕着嘴唇转了一圈儿,它似乎饿了。
白玉京走到了床头,掀开了床榻,下面是一身衣服。
黑气就是从此处散发出来的。
白玉京拾起衣服问道:“邢掌柜,这件可是令爱的衣服?”
邢望探头看了一眼道:“正是,阴阳先生说,死者临走时穿着的衣服会带着死者的冤魂,为了让她头七之前莫要离开,贴身衣物要放在床上,待头七之后,随棺入土。”
白玉京缓缓点头,听得明白,邢掌柜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这件衣服是不可能拿走的。
他也没打算拿走,只是摆弄着这件衣服,隐隐看去,发现这黑气是从袖口和胸口处传来的,于是手中匕首轻轻一划,用极快的动作将袖口的布条取了下来,放入自己的口袋里,这才再将棉被盖上,不动声色地走到门口道:“邢掌柜,我看完了。”
邢望的脸上是难掩的失望,“可惜了,小女走得早些,县尉楚大人说过,这是小女命数如此,可是……我一直都不相信,小女从小到大无病无害,怎么可能走得这么简单?兴许是瘟疫吧,这些年走的姑娘也不算少了。”
白玉京问道:“走了很多?”
邢望道:“是啊,这个月走了两个,便是小女和东城的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的女儿在出嫁的路上死了,和小女如出一辙,只不过比小女早走了半个月。”
白玉京道:“两个?”
邢望摇了摇头,压着声音道:“此乃是天意所为啊,天痕出现,便就是应征了老天收人,每个月都要收一个二八少女,且都是将要出嫁的,从年前就开始了,现如今……哎,已死了十一个了吧。”
白玉京啊了一声,“每个月死两个,怎么会是十一个?”
邢望道:“大人你不知道啊?有一个姑娘虽然死了,但等到下葬的时候发现,竟然是一口空棺!人不知道哪儿去了,后来有人说在余杭县后面的崖山上见过她……啧啧啧,兴是尸骨未寒,想念夫君,这才魂魄带着肉身出窍了吧。”
白玉京问道:“您可知道这是哪家姑娘?”
邢望道:“是城北施家的闺女,她家老爷子是做布料生意的,和我也算是打过交道,嗯?不对啊,这个施家丫头,应该您熟悉啊。”
白玉京不解道:“我怎么会熟悉?”
邢望吸了口气,“我不该记错啊,那施家丫头,不就是要嫁给县尉大人的吗?”
白玉京顿时一怔。
正当此时,管家跑了过来,喊道:“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那陈公子又来了。”
白玉京问道:“陈公子?”
邢望解释道:“大人,这陈公子原本是我的姑爷,可现在……哎,他与小女情投意合,二人爱慕已久,这才许下婚约,陈公子家乃是书香门第,因为陈老爷子不计这门庭之别,我才得意高攀,本以为就此可以跻身余杭县上流,可谁知……哎。”
邢望伸手请道:“我得去看看陈公子,听闻这几日他茶饭不思,追着要见我家小女,还要家里许什么冥婚,真是痴心之人啊,出了事可不好了。”
白玉京道:“我随你一起去看看。”
到了前门,看到了一个书卷气的少年,他已趴在灵堂之内棺椁上,痛哭流涕,见到此情此景,邢望也忍不住泪声俱下,似乎刚刚平复的心情又被勾了起来,上前劝阻。
白玉京也不知该如何,想到这里也已没有什么事,便打算离开,刚转头,看到那个披着孝袍的小女孩蹲坐在地上,双手扶着下颚看着面前的一切,眼神里似乎大有不解。
白玉京走了过去,也跟着蹲下,“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女孩歪着头道:“我叫邢妹儿。”
白玉京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你在看什么?”
邢妹儿指着趴在棺材上的少年道:“我在看他,在看他假慈悲!在看他讨人厌!”
白玉京看着邢妹儿脸色变得气愤,当下觉得不太对劲,问道:“他怎么假慈悲,怎么讨人厌了?”
邢妹儿道:“哼!若非他前一天晚上偷偷来到我家,带着我姐姐出去,我姐姐就不会第二天死了!”
白玉京立刻追问道:“你亲眼看到是他?”
邢妹儿指着陈公子腰间的扇子说道:“他那把扇子是我姐姐亲手给他做的风雨瑶心扇,天下独一份,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了那把扇子。”
她仰起头道:“阿娘说我长大了,不该总和姐姐在一起睡,可我还是想姐姐,所以那天晚上我趁着阿娘睡着,偷偷跑到了姐姐的房间里躲在床下,就看到他送姐姐回来,等他走了之后,无论我怎么叫,姐姐都不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