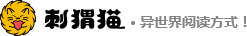最终,陈平不仅混了个肚子饱。
临走时,还打包了一小笸箩的花饧。
当陈平端着笸箩回到库房,叶老已将杂乱的账簿分门别类,做了简单的归纳。
他走近一看,账簿上有条不紊的画上了数条碳痕。
看似杂乱,实则一笔一划皆有考究,在他眼中隐隐编织成一张蛛网,坐等捕获那些县衙蛀虫。
但叶老却暂未声张,在拿到切实的铁证之前,所有的一切,在外人面前都只是猜测罢了。
而且极有可能打草惊蛇。
唯有万事俱备,才好斩草除根,不留隐患。
陈平看到叶老满脸愁容的样子,也自然知道了事情有多严重,便把花饧捧到叶老面前。
“老师,您也尝尝,这是那些人给咱们的孝敬。”
叶老抬头看见是陈平,如墨般的脸色也稍稍明朗了一些。
不过,他年岁已高,实在是不敢挑战甜度这么高的东西了。
一个不注意,说不定牙都要被粘下来几颗。
先是摸了摸陈平的脑瓜,又没好气的弹了两下,“我虽然不屑于和这些污吏有交情,但这东西老夫可真吃不了。”
话锋一转,步入正题,“说吧,今晚有什么收获?”
多次见识了自家弟子的奇异表现,加上此次事态紧急,不得不使让陈平放开手脚发挥了。
只见陈平人小鬼大的模样,就知道他肯定弄来了干货。
不出所料,待陈平说完今晚听到的对话后,叶老登时拍案而起,反复喃喃道,“终于让我抓住这些老鼠的尾巴了。”
这一起太快了,叶老又是年近甲子之人,忽然间有点头晕眼花,腿脚都不稳当了,陈平见状赶忙上前搀住。
他摆摆手推开陈平,先是在房间内转圜了一圈,又回到案前坐下拿起了笔。
不一会,一封仅有百字的密函,挥墨而成。
叶老捧着这一张纸,没谁比他更清楚,这一封密函有多重的分量。
脸色阴沉的抬头望向陈平,严肃的说道:“从此刻起,这件事情你不必再插手,也绝不能告诉别人你今日的见闻。
这封密函的一句一字,都是我调查出来的,和你没有半文钱关系,记住了吗?”
陈平何等聪慧,怎能不知这是叶老在保护自己。
他明白,就算王县令拿到了切实的证据,也只能做到杀鸡儆猴,绝不可能将县衙涉事的一干人等全部处理掉。
毕竟县衙又不是王县令私产,无论是本地的士绅,还是上级州府衙门。
都不会允许王县令,在一县之地,唯我独尊。
否则,那岂不是成了,实打实的百里侯!
当各方势力再次达成平衡之后,那些被迫吐出巨大利益的胥吏们,心里必然会有强烈的怨气。
到时候,若是让他们得知陈平参与了此事。
极有可能会有莽撞之辈,不顾及叶老的名望,直接使出下作手段来。
哪怕只有那么一丝的可能性,叶老也不会拿陈平的安危来冒险!
陈平懂事的点了点头,保证今后不再过问,也不再掺和。
......
入夜,沾床就睡的陈平,却不知外面雨疏风骤。
先是赵都头踏着夜色,取走了这封重如千钧的密函。
夜半三更,一伙人潜行到一家米库门口,扇年久失修的木门如响雷般被敲响。
四更,米库掌柜的口供,被秘密送到了王县令的手上。
五更天,一个铁器铺的东家和一个石料堆栈的掌柜,一起被押进了牢房。
六更天,一处许久无人居住过的小院,已被查抄一空。
晨曦初露之时,位于县城东侧,一处许久无人居住过的小院,已被查抄一空。
朝阳初升之际,被胥吏贪墨掉,尚未来得及处理的值钱物料和工具,全都堆在了县衙里。
这一夜,堪称雷霆手段,足以躬耕纯火,涤荡宵小。
赵瑾带着十几个衙役,手持铁尺,闯进了修路工地。
此时的陈平刚搓开惺忪的睡眼,艰难地从藤床上爬了起来,便听到了外面嘈杂的声音。
其实昨晚他心中就大致有了个底,所以也就没有太过惊讶。
只是浅浅抱怨了一句:“真晦气,大好的清晨都没法看书了。”
陈平大概猜到了是何事,却也没有太过关注。
只是随口抱怨着,“真晦气,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了!”
库房门口,几个人跪在地上,心理脆弱的已经瘫坐着在抽泣。
他们心里都清楚,经过今日这一事,县衙是别想再待了,能重返白身都算是王县令法外开恩。
严重的恐怕会被判充军边境,那无疑是九死一生。
这几个倒霉蛋,看面相是老实巴交,属于连油花都捞不到多少的底层人物,却被率先拉出来示威。
引得尚未出工的民夫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指指点点。
不过多时,众人从小声的议论中,冒出一阵鼓掌叫好的声音,围观的人经这一起哄,纷纷拍手称快,像是在围观一场大戏。
不多时,王县令来到了众人面前,身旁站着赵瑾和衙役。
他阴沉着脸,指着那群跪地上的蛀虫悲呼道。
“黔首困极,何物极而不反?胥吏戾恶,竟祸内而敛财!本县承平之治,风调雨顺,未有外敌,先诞内鬼,本为利民之举,何为蠹木之梁!
都言本县旧路难行,数十里泞泥崎岖,又怎甚于攘内之途?
贪官污吏不绝,如猛虎潜伏于途;足下风气不正,如经风雨而无所庇护。
人人雁过拔毛,既如此,康庄大道,何日可见!
吾辈困厄科场,也未觉今日这般掩噎难言,恨不得罢官还乡,埋骨桑梓!”
王县令已经多年未做诗词,以至于周围的不少人都忘了他曾经也是大才子,文道乃心声,此时的内心或许从未如此吵闹过。
“无耻至极!!!”
愤愤的落下这一句后,王县令就背过身去,吩咐道。
“取纸笔来,本官要把这些蛀虫做的恶事,尽数禀告府衙,上奏朝廷,定要治他们个流放抄家之罪!”
声音如炸雷般响亮,显然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
赵瑾不敢多言,只好捧出事先备好的笔墨走上前。
可王县令身边的县丞和主簿,却不敢再沉默下去了。
先是县丞悄然上前一步,低声劝解道,“县尊且慢,此事万万使不得!”
“我永顺县的事情,只能在县里解决,若是惊扰到了哪位御史,只怕会节外生枝”
“就算他们最后被判了抄家流放,县尊怕是也会落得个御下不严之罪啊!”
县丞的语气虽然轻缓,可话语却着实犀利,一下点到了痛处,令正在火冒三丈的王县令,也不得不考虑一下这些现实的问题。
另一旁胆子小的主簿,两腿已经颤颤巍巍了。
年岁半百的主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做了一辈子胥吏,竟也会落得个晚节不保的地步。
今日一早,他就被传唤到了县衙里,当看到满地堆积的物资和工具,就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王县令也未听他辩解,直接就叫赵瑾将人绑了过来。
堂堂一县主簿,就这样当着数千人的面,噗通一声跪倒在了王县令身前。
“是下官猪油蒙了心,请尊上开恩,饶我这条贱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