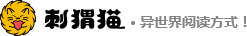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见过四殿下。”
楚识夏抬眼细细地打量白子澈,只觉得他眉眼确实像极了皇帝,湿润沉静。白子澈一身书生似的打扮,为了抱怀里的画,淋湿了大半个肩膀。
“楚姑娘这是要出宫吗?”白子澈道,“这雨越下越大,楚姑娘若不嫌弃,可到画院里坐坐。”
出了宫,无非就是去羽林卫或回秋叶山居。楚识夏想起梦中往事,又思及沉舟湖水般的眼,心中思绪万千,便起了逃避的心思。
“那就叨扰四殿下了。”
一地狼藉的画院里被草草地收拾了一通,侍奉的小宦官和画师们见了楚识夏,都心有戚戚,不敢多说。
白子澈大约是摔打着长大的,照顾自己和照顾别人都信手拈来。他妥帖地收拾了身上的水渍,又给楚识夏端了杯姜茶。白子澈的指腹上有洗不干净的颜料,五彩斑斓。
“四殿下折煞臣了。”楚识夏接过热姜茶,低声道。
“楚姑娘不必如此客气,我本来就与其他皇子不同。楚姑娘救我一次,我却没有什么可以作谢礼的,是在惭愧。”白子澈语带恭谦,却不卑不亢。
楚识夏向来知好歹、懂进退,知道这种话说的人可以当真,听的人却万万不能得寸进尺,便道,“殿下言重了。”
画院的白墙上爬满了青苔,墙头上有爬山虎挂下,一片绿意盎然。
楚识夏捧着热姜茶暖手,坐在檐下看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地上。她背后的画院里,宦官们忍气吞声地整理清点被毁掉的画卷,白子澈竟然也纡尊降贵地去帮忙。
画院中珍藏众多,三皇子一番打砸,受损的不止有画师们的作品,也有不少大家名作。
“完了完了,”年少不经事的小宦官一屁股坐到地上,哭天抹泪道,“毁了这么多画,几条命够赔啊?”
这句话说出了众人的心声,一众画师都沉默不语,有意无意看向白子澈的眼神都带了幽怨。
“若不是四殿下你画了那副画,惹得三殿下不快,也不会有今日的灾祸。”
不少人在心里这样想。
可他们不敢说出来。白子澈再落魄也是皇子,三皇子可以打骂,朝中权势正盛的世家子弟也可以轻慢,但身为下人的画师和宦官却不可以。
“四殿下画的那副画,究竟是什么?”楚识夏忽地插进来,问,“我瞧着,上面是个人。”
“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白子澈摇摇头,“我只知道,那是个美人。画院的珍藏阁里有不少为她作的画像,但父皇说,难仿真人神韵一二。我揣摩旧作,画了那副画,故而得父皇赏赐。”
楚识夏装糊涂道,“可我看殿下穿着朴素,并不像得了赏赐的样子。”
白子澈犹豫片刻,才说:“父皇的赏赐,我都散给了画院的画师杂役了。我出不了宫,也不没有下人可打赏,留着没用。”
画师们闻言都不安地扭开了头,似要躲避楚识夏的目光。
楚识夏便笑开了,“我看大家伙神色,还以为好处都许了殿下一个人,惹来祸事却要众人一同担当呢!”
这话刁钻又刻薄,羞臊得还要脸面的人心下发虚。
年老些的画师在那小宦官头上拍了一下,恨铁不成钢道,“难道哭一哭便能将这些画哭好么?还不快起来干活!”
——
这场雨下了很久,楚识夏一杯热姜茶下肚,竟然坐在椅子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她睡梦中察觉有人靠近,带得一阵风起,警觉地扣住了那人的手腕。
“谁?!”
“是我。”白子澈不慌不忙地松开手指,替她盖上薄毯。
“抱歉,臣睡懵了,多有逾越。”楚识夏歉疚道。
“无碍。”白子澈在她身边坐下,“这雨下得很大,要不要派人出宫报信,叫楚姑娘的家人来接你?”
“等雨停便好。”楚识夏正好落得个清净,无所谓道,“那些画,殿下打算怎么办?”
“有的尚可补救,有的……我也没有办法。”白子澈摇头道,“回头向父皇请罪便是。”
“三殿下打砸的画院,为何要四殿下你去请罪?”楚识夏脱口而出,才觉此话鲁莽。
“我虽为皇子,却自小就知道,我和其他兄弟姐妹是不一样的。”白子澈一笑,笑容洒脱,“即便我告了三皇兄的状也无济于事,反倒叫他记恨我。但我若不领了这罪名,受难的就是画院的画师杂役。”
白子澈眨眨眼,笑道,“受罚便受罚吧,总不能真的杀了我。”
楚识夏这回没接话,只是笑了笑。
“四殿下,有件事臣要提醒你。”楚识夏若无其事道,“三殿下今后恐怕会锲而不舍地找你麻烦了。”
白子澈一愣。
三皇子没有那么闲,会关注每日有几幅画送到了未央宫,皇帝又钟情与哪副画。他暴跳如雷,定是因为此事触到了他的逆鳞——无非是东宫和皇后。
一个画中仙,怎么会得罪皇后呢?
必然是有人投机取巧,见皇帝迷恋画中人,便去民间寻找相似的女子。
宫中已经有了一个容妃,皇后已然门庭冷落,靠着陈家威势才没被人踩在头上为所欲为。
若再来一个,即便弄巧成拙,并不得皇帝宠爱,于皇后而言也是一件很恶心的事。
就算白子澈是无心的,三皇子也不会放过他。
更何况三皇子根本不是讲道理的人。
——
秋叶山居。
楚识夏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玉珠为她端来姜茶,却被她推开了。
“我在宫中喝过了。”楚识夏道。
玉珠只当宫中伺候的下人仔细,便没有多想,只是将她带回来的君子兰安顿在房中。
“我的大小姐,您下回眠花宿柳,打发个人回来知会一声可好?”玉珠挖苦道,“今早宫里的人来,愣是没人敢接旨。还是羽林卫的邓勉公子来送信,说您抢了芳满庭的姑娘游湖,一夜未归。”
“宫里出来的宦官细皮嫩肉的,哪里会骑马?”玉珠责怪地看她,“被您的亲卫带到马上一顿呼喊,下马的时候上吐下泻,您不会没看见吧?”
楚识夏心虚地摸了摸鼻头,企图狡辩,“我年少不懂事,总有借酒浇愁的时候。”
“有什么愁也不能不回家啊!”玉珠提高了嗓门,“外头竟有如此逍遥么?二公子最混账的时候,也不敢抢了人家花楼的姑娘夜不归宿啊!”
玉珠说到这里又有些后悔,若是在云中,楚识夏绝对干不出这样轻狂浮浪的事来。可楚识夏偏偏就离了云中,这话恐勾起她思乡之苦。
楚识夏完全没被勾起思乡之苦,连连告饶,脚下立刻退出了卧房。
雨后空气清新,楚识夏慢悠悠地晃到湖边的亭子里,趴在栏杆上望着一池破碎的月色。四下里静悄悄的,然而楚识夏知道有个人一直跟着她。
沉舟就像是她的影子,前世今生加在一起,跟了她二十余年。
割舍一个影子,竟也有破皮断骨之痛。
楚识夏在心里笑自己自以为是,理所当然地把沉舟划作了自己的东西。
“沉舟,我有话要和你说。”
浓墨般的阴影里走出一个人来,沉舟静默地站在她面前,两人之间隔着三尺的距离,一伸手就可以够到对方。然而楚识夏却觉得,这是她一生都无法越过的沟壑。
沉舟固执地不肯靠近楚识夏,不知道是因为她在那个吻之后袖手离去,还是因为她一天一夜没有让他跟着。
别扭得有些可爱。
楚识夏笑出了声,抬手道,“你过来。”
沉舟磨磨蹭蹭地往前走了一步,被楚识夏攥住衣领,带得躬下身来。楚识夏在他微凉的唇上落下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两人之间呼吸可闻。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楚识夏在这样近的距离上凝视沉舟的眼睛,像是在看一对墨色的冰晶,心脏不由自主地乱了节拍。
“这世上,只有两情相悦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还有邓勉给你看的书上的事。”楚识夏一字一句,用尽了生平所有的耐心,教导沉舟情爱二字。
“两情相悦,就是你爱一个人,她也爱你。你们之间没有秘密,没有欺骗,你想和她过完这一生,无论家世、病痛或战乱的阻隔。她可以为了你拼命,你亦然。”
“你会三茶六礼、八抬大轿、明媒正娶迎她进门。她会是你的妻子,你们会相濡以沫地过完这一生。”
楚识夏绞尽脑汁,搜寻着世间佳偶的典故,要为沉舟寻一个古今以来最好最好的爱情楷模,“就像……《凤求凰》和《白头吟》,就像兄长与我们说的那棵枇杷树。”
沉舟从恢复五感之后就和她一起读书认字,俨然是当世家小公子培养的,无怪乎邓勉会说他是楚识夏的童养夫。
他自然知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也知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年幼时学过的诗文沉舟并不理解其情深,其意切,却在楚识夏的颤动的唇间感受到了痛。
沉舟安静地听着,像是要穷尽这一生的智慧去理解她的每一个字,去领略世人甘之如饴的情爱。
“你……懂了吗?”楚识夏问出这句话,却不敢看沉舟的眼睛。
难以呼吸的痛苦攫取了沉舟的心脏,他俯视楚识夏蝶翼般颤抖的睫毛,想要伸手抚平,却又不敢。
他生平何以胆怯至此。
不要难过了。沉舟在心里说,你不要我亲你,我就再也不亲了。
你不要哭。
楚识夏只是察觉了沉舟点头的动作。
“以后不许再这么亲我,也不许亲别人了。”楚识夏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细小的刃,一遍遍凌迟她的心脏,“否则你将来的娘子会不高兴的。”
那样漂亮的唇,以后会是谁的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