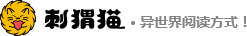卧房桌案上的瓜果点心都被楚识夏抱在了怀里,她盘腿坐在地上,拎起一只皱巴巴的橘子放到桌上,道:“这是摄政王,帝都权势最盛的人,势力盘根错节。如今帝都局势紧张,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人,不能杀。”
沉舟抱着剑,面色看不出喜怒,只是点了下头。
楚识夏又拎出来一只饱满的橙子,说:“这是太后,摄政王的亲生姐姐,陈家嫡出的大小姐。这个人,不能杀。”
沉舟还是点头。
楚识夏翻翻拣拣出一枚核桃,放在橘子和橙子中间,“这是陛下,陛下不是太后亲生的,据说他的亲生母亲是个宫女,不过他对外都说自己的母亲是尊贵的陈家嫡女。陛下想要亲政,所以他会非常想拉拢楚家。这个人,也不能杀。”
沉舟点头。
楚识夏又找出来一只香梨,“这是首辅,他......”
“不能杀。”沉舟打断了她。
“对。”楚识夏满意地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杀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今后在帝都,你不要轻举妄动。”
“杀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是因为杀得不够多。”沉舟神色冷漠,“这些人不是不能杀,只是暂时不能杀。”
换个人坐在这里,已经被这番大逆不道的话惊得屁滚尿流了。
但楚识夏双手向后一撑,笑得轻松写意,“沉舟,大周养士百年,刺客暗卫数不胜数,不止楚家有,帝都也有。纵然我有心让你去杀,你真的能杀掉他们吗?”
“只要你说,我就能。”沉舟的目光从一桌子的橘子梨子上扫过,像是已经把它们开膛破肚,露出淋漓鲜美的汁水来,“先杀哪个?”
楚识夏笑得更开怀了,她摩挲着手腕上的佛珠道,“沉舟,造杀业是要入无间地狱的。纵然你不怕,我也舍不得。”
沉舟生生地按下去了要比划出“我不怕”三个字的手。他分明没有打手语,面上也没有一丝波动,楚识夏却莫名觉得他有几分雀跃。像是被捋顺了毛的小猫。
这时房门忽然被人敲响,传来玉珠的声音,“大小姐,宫中容妃递了帖子来,邀您进宫赴宴。”
——
容妃是皇帝的嫔妃中最得圣宠的一位。
据说这位容妃生得美艳动人,无论是谁被她轻飘飘地看一眼,都会酥到骨子里;又说她妖媚惑上,心肠狠毒,以色侍人早晚没有好下场。
“如今的东宫是陈皇后的长子。容妃并没有子嗣,身后也没有倚仗,所以今日的宫宴应该是陛下的意思。”
街道上影影绰绰的灯光透进马车里,楚识夏闭着眼睛,指尖一颗颗地从佛珠上抚摸过去。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皇帝或太后接到宫里住着,日日受人监视。
楚识夏心道,必须尽快将沉舟安顿好。
“马车上是谁家的小娘子啊?出来给本公子唱个曲儿,否则今晚这条路你便别想走了!”
马车停下了,楚识夏听见马车外的护卫抽刀的声音。她打起帘子探出身去,呵斥道,“把刀收起来,这是帝都,不要妄动兵戈。”
楚识夏抬眼看向拦在马车前的几个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公子哥,有的人腰上还系着禁军的腰牌。他们骑着马,胸前的甲胄散开,像是刚刚离值的模样。
“好啊,公子想听什么?”
楚识夏盈盈一笑,她穿着天水青的衣裙,外头压着雪白的鹤羽大氅,如云般的鬓发剑斜斜插着几根玉簪。她这一笑在月光下仿佛透明,雪光潋滟。
几个纨绔都看呆住了。
楚识夏缓步走下马车,伸手抚摸着最前面那匹马儿的鬃发,“原来是北边驯服过来的雪鬃马,我说怎么如此眼熟。”
“小娘子好眼光……”马上的纨绔色眯眯地伸手去抓楚识夏的手,却被她避开了。
楚识夏笑得更灿烂了,“当然,云中的马,我怎么会不认识?”她猛地拔下发间的玉簪,穿透纨绔的手掌,将其狠狠钉在了雪鬃马的脖颈中。
纨绔的哀嚎被淹没在骏马的嘶鸣声中,雪鬃马前蹄高扬,当即就把马背上的人摔了下来。楚识夏拔出玉簪,雪鬃马重重地倒在地上,街上的行人尖叫着跑开了。
楚识夏扔下玉簪,蹲下身拍着他的脸说:“我是云中镇北王府楚家的,公子可不要错认了。”她看向这人变形扭曲的左腿,嫣然一笑,“当然,我相信你们没有找错人。”
如果方才她的护卫们动手了,少不得有人顺理成章地撤走这些粗鄙无文的护卫,然后为她派遣更“合适”的人选。帝都遍地名门权贵,这样随意拦下女眷马车的登徒子能活到今天,绝非侥幸。
纨绔在剧烈的疼痛中睁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我们走,莫要让容妃娘娘等急了。”
——
楚识夏换了另一身衣裳,用沾水的手帕重重地擦着脸颊和手上的马血,动作粗暴。
“大小姐,您是在擦铁锅吗?”玉珠忍不住道,“还是让我来吧。”
楚识夏吐出一口气,把手帕扔给她,语焉不详道,“云中的战马到了帝都,也难免变成花架子啊。”
玉珠没听懂,温柔道,“您方才不该动手的,让人见了又要说王爷没有教好你了。”
“楚家的女儿蛮横骄纵,比心思深沉更让他们放心。任性又愚蠢的人破绽百出,最好拿捏。总要留点错处给他们挑。”楚识夏厌烦地掩下睫毛。
不多时,马车便入了宫。
容妃的春鸾殿装潢华丽,空气中弥漫着温暖的苏合香。
隔着重重叠叠的珠帘,楚识夏只看见一点丰腴鲜艳的唇,衬得肌肤愈发的白。珠帘后的人斜斜地倚在榻上,薄衫下起伏的曲线如同连绵的春山。
“识夏来了。”容妃的声音慵懒缱绻,“说起来,我也算北方人呢,刚来帝都时还水土不服了很久。识夏在帝都这些时日可还习惯么?”
楚识夏觉得容妃有些像她记忆深处的香姨娘,话尾带着钩子似的,不大自在道,“甚好。”
“帝都的冬天也下雪,不过比起云中的雪,还是差了许多。我不缠着你了,你去前头和年龄相仿的闺阁小姐们说说话吧。”容妃含笑道,“帝都五湖四海的人都有,能说话的人却少。若侥幸得一个说得上话的,日子便不会太难熬。”
楚识夏装聋作哑地见了礼,转身出去了。
春鸾殿前头摆的宴席还未开始,帝都的名门千金们彼此相熟,叽叽喳喳地说话。
楚识夏百无聊赖地听着,聊的无非是哪家铺子新出的胭脂水粉衬气色,流云锦和织羽锻谁更胜一筹,谁家的公子和谁家的女儿又订婚了。
偶尔有几个出现在楚明彦手写名单上的名字,楚识夏才勉强打起精神来听。
“楚识夏,你在帝都过得还习惯么?”
这声音倨傲,每个字的语调都微微拔高,透着种居高临下。
楚识夏停下了摆弄佛珠的动作,抬眼望去。
她的位置被安排在最接近主位的地方,发话的那位位置和她相对。那是个容貌姝丽的少女,穿着一身张扬的红衣,那些聊天的小姐们都有意无意地簇拥着她。
“还成吧。”楚识夏随口道。
少女咄咄逼人,“听说你在城门口对苦主大打出手。我知你自小父母双亡,无人教养,可帝都是天子脚下,容不得你放肆。”
幸好指桑骂槐的是老镇北王,否则楚识夏的杀心又要起了。楚识夏在心里假惺惺地念了声佛。
“说得好像你亲眼看见我打人了似的。”楚识夏一挑眉,“还有,这位……婶子,您下次问别人话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报上自己的家门姓氏?”
“你叫谁婶子呢!”少女拍案而起,头上的珠翠哗啦啦的响,“你敢侮辱我,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
“我不知道。”楚识夏微微向后倾,摆出一个放松的坐姿,“不过我看你对我的父亲很了解,怎么,你想给他做续弦?”
“楚小姐慎言,”一个贵女疾言厉色道,“这位乃是摄政王膝下六小姐。”
陈六小姐的姑母正是当今太后,姐姐是今上的发妻,表哥是东宫太子。容妃得宠,碍了太子和皇后的路,陈六小姐本不屑参加这场宫宴。
但她的目标是楚识夏。
摄政王府上下都在传,楚识夏杀了摄政王府的幕僚。陈六自小众星拱月长大的,见不得人辱陈氏门楣,收到容妃虚情假意的邀帖后,当即决定进宫给楚识夏一个下马威。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摄政王亲临呢。”
楚识夏笑道:“分明是陈六小姐先出言不逊,怎么只警告我一人谨言慎行。莫非云中楚氏穷乡僻壤,和帝都公卿的女眷们同席只能赔笑,你打我左脸,我便要把右脸也凑上来么?”
“我们只是闲聊罢了,楚小姐何必说得如此严重。”那代替陈六报上家门的贵女心有戚戚道。
楚识夏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原来帝都时兴这样的‘闲聊’,改日家兄进京述职,必当把家父刨出来和各位小姐们好好‘闲聊’。”
名门贵胄之间哪怕冷嘲热讽,也不肯失了仪态,像市井泼妇一样扯着头发对骂。这些大小姐们哪见过楚识夏这荤素不忌的说辞,又气又没法接话,脸都憋红了。
“怎么,不聊了么?”楚识夏扫她们一眼,反客为主道,“不聊了就坐下吧,都站着我还以为你们要给我布菜,识夏可受不起这样的大礼。”
陈六小姐忍无可忍地怒吼一声,踹翻了桌子,拂袖而去。